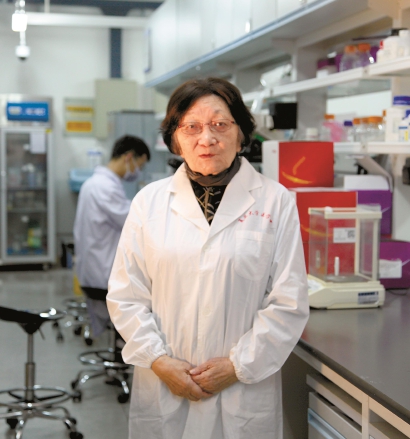
中国工程院院士闻玉梅是我国著名的病毒学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暴发后不久,她就发表了相关研究论文。最近,她又与11位院士联名向广大市民发出了应对疫情的倡议。 86岁的闻玉梅与病毒打了一辈子交道,面对重大疫情,她曾多次以身涉险,甚至用自己的身体做试验。 在她看来,人与病毒的抗争,是永恒的课题,也是不断的考验。人与病毒之间的平衡共生,需要依靠科学,更需要智慧来理解与认识。 拐点的到来要靠每个人的努力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拐点主要有以下两个特征:一是新发的疑似感染病例下降,二是确诊的发病患者数量下降。 ●我国还没有发现新型冠状病毒的突变,至于什么时候突变也无法预测,当下关键还是要做好防控和治疗。 解放日报:随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确诊人数的不断攀升,大家目前最关切的,就是疫情的拐点何时到来。您在几天前的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拐点的到来需要两周到一个月,这一判断是基于什么? 闻玉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拐点主要有以下两个特征:一是新发的疑似感染病例下降,二是确诊的发病患者数量下降。 拐点的到来要靠每个人的努力。政府采取严格的防疫措施,每个人都严格遵守这些规定。除了奋战在一线的医务人员之外,我们看到还有许多疾控工作者、志愿者正在奋斗,我真的很感动,没有他们的努力,疫情是很难控制的。正是因为全社会都在积极行动,我才敢于说,疫情会有拐点。 解放日报:随着春节假期的结束,人员的流动是否会引发二代传播的新高峰? 闻玉梅:只要人们在回城的时候,都严格遵守国家的要求,积极配合检查,根据需要做必要的隔离或留察,即使有二代病例,也是散发的,不会形成高峰,没有必要惊慌。希望大家不要歧视返城人员,返城的人也要认真执行地方的规定。 大家最近都很焦虑,前几天我看到一位快递员和保安吵了起来,甚至还动起了手。我劝他们,这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要好好遵守应有的行为准则。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人与人之间更需要互相谅解,人心不能疏离。 解放日报:许多地方出现了无湖北接触史的病例,比如有一个病例没有外出史,但住在确诊患者的楼上,由此引发了不少人的担心。您怎么看? 闻玉梅:无湖北接触史的病例目前总体而言还是散发的,是可控的,没必要恐慌。我们需要有一个全局观念,不要以点概面,要用科学的态度来看待疫情。 如果所居住的小区或者大楼里有人患病,要提高警惕,但不要过度紧张。要避免病毒的呼吸道传播,戴口罩是比较有效的手段。要避免接触传播,则要留意电梯按键、门把手等,要勤洗手、正确洗手。现在有些居民楼里准备了专门用来按电梯的纸巾,这很值得提倡。此外,戴手套也是一个有效手段,但使用过的手套必须进行消毒。 解放日报:新型冠状病毒会不会变异?变异之后的毒性会否增强? 闻玉梅:根据科学规律,病毒的变异是必然的。新型冠状病毒的复制速度非常快,病毒的基因会在复制过程中产生变化,但它的毒性有可能增强,也有可能减弱,有些突变也有可能是无意义的,科研人员必须跟踪它基因组的变化,不断监测。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发现新型冠状病毒的突变,至于什么时候突变也无法预测,当下关键还是要做好防控和治疗。 从来没有一种传染病会把一个国家的人打倒 ●焦虑会使人失去对谣言的基本判断,而恐慌引发的抢购、排队,肯定是对控制疫情不利的。 ●病毒对人类的侵袭是不会停止的,以后一定还会有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经过这场考验,我相信我们全社会的素养和能力都会提高。 解放日报:互联网上有海量的疫情信息与各种提醒,其中也掺杂着不少谣言,很多老百姓无从分辨,从而引发恐慌。您曾经历过许多重大的疫情,恐慌的情绪会对疫情的控制产生怎样的影响? 闻玉梅:现在必须给大家焦虑的情绪降降温了。焦虑会使人失去对谣言的基本判断,而恐慌引发的抢购、排队,肯定是对控制疫情不利的,无论是对个体的健康,还是对政府的措施,都会造成影响。 比如有些人一发烧就很担心,马上到医院的发热门诊去排队,这可能会造成交叉感染。现在上海有多家医院都开通了网上发热咨询,这是非常好的措施,充分利用了互联网的优势。 解放日报:还有人一听说什么药能预防或有助于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就立即去排队抢购。 闻玉梅:我还是强调,要有理性的、科学的态度。免疫力的提升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离不开健康的生活方式。今天抢购这个药,明天排队买那个药,都是很不明智的。 在疫情的关键阶段,大家要冷静,要稳住,要相信我们一定会成功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一种传染病会把一个国家的人打倒。大家要相信历史、相信规律。 天花曾经是全世界最严重的传染病之一,最后人类靠疫苗战胜了它。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西班牙大流感在全世界造成的死亡人数比战争致死的人数还多,停战后不久,就得到了控制。2003年非典肆虐我国,我们最重要的防控措施就是隔离。那时候我和钟南山院士以及香港的科学家一起研制了一种滴在鼻子里的疫苗,想尽快给大家用上,可还在等待审批的时候,非典就基本结束了。疫情的控制是有一个过程的,就像我们生了病以后,它有一个高峰期,然后就是恢复期。 我们中国人是非常有智慧的。鼠疫在全世界夺走了数亿人的生命,远超过全球历次战争死亡人口的总和。1910年末,哈尔滨暴发鼠疫,20多天就传遍了东三省,平均每月死亡一万人。那时候国际医学界普遍认为鼠疫是老鼠身上的跳蚤携带病菌传给人类的。然而东三省的官民几乎把耗子抓绝种了,瘟疫并没有得到遏制。有一个名叫伍连德的马来西亚华侨提出,鼠疫有可能是通过呼吸道传播的,他提倡大家戴口罩,还发明了一种棉纱口罩,就是在纱布里面放一块吸水药棉,被称为“伍氏口罩”。 当时的东北没有隔离病房,但东北的铁路比较发达,伍连德就用一节节独立的火车车厢做成隔离病房,最终控制了疫情。 解放日报:对于个体而言,最难的是如何实现合理的重视与不必要的恐慌之间的平衡。 闻玉梅:确实如此。疫情对全社会的科学素养、心理素养都是一场巨大的考验。病毒对人类的侵袭是不会停止的,以后一定还会有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经过这场考验,我相信我们全社会的素养和能力都会提高。 病毒也有两面性人与病毒亦敌亦友 ●面对一种新的病毒,防控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科研,这两者缺一不可。等疫情过去,科研依然不能放松。 ●人与病毒之间的平衡共生需要依靠科学,更需要智慧来理解与认识。从战略上要知道,它必然会与人共存,在战术上也要做好准备。 解放日报:新型冠状病毒是否比SARS病毒更“狡猾”?2003年我们抗击非典的经验对这次的疫情有怎样的借鉴意义? 闻玉梅:非典为这次疫情的控制提供了很多的经验,比如在隔离以及治疗方面等。现在的诊断速度和治疗手段比当时都大大提高了,我们也很希望这次的疫苗研发可以加速。 对于新型冠状病毒,我们还没有完全了解。就目前的发病数据来看,它的传播性比较强,但是致死率不高。与非典相比,轻症患者较多,有部分患者感染了却不发病或症状轻微。但是这种病毒在潜伏期也有传染性,有些患者没有症状,也会传播。至于它的发病机理、将来会有什么后遗症等问题都还有待于研究。 面对一种新的病毒,防控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科研,这两者缺一不可。防控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但我认为科研是防控疫情的重要基础,是不可忽视的。通过科研不仅可以产出有效的防控手段,如发现新药物、新疫苗,还可提高其他传染病的防治水平。等疫情过去了,科研依然不能放松。 解放日报:包括非典在内,近年来的禽流感、中东呼吸综合征、埃博拉病毒等重大疫情不断,病毒对人类的杀伤力是否越来越强了? 闻玉梅:人与病原体之间的抗争,是永恒的课题。新的致病微生物必然会不断出现,可是人类也会在斗争中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本领。人类与微生物病原体之间是相辅相克的,抗疫战争是不会停止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解放日报:如何理解您所说的“相辅相克”? 闻玉梅:病毒听上去很可怕,但它也有两面性,可以说是亦敌亦友。我们可以利用病毒做成疫苗,有些制品也可以通过基因工程以病毒来表达。我今年开了一门网络课,就是讲“病毒的利与害”。 人与病毒之间的平衡共生需要依靠科学,更需要智慧来理解与认识。从战略上要知道,它必然会与人共存,可是在战术上也要做好准备,它来一次,就能够反击一次,不断提高自己的反击能力。 解放日报:近年来有不少引发严重传染病的病毒都是由动物传播给人类的,这是否与人类的行为有关? 闻玉梅:病毒的传播和人类的行为确实息息相关。2003年,西尼罗病毒在美国爆发,有8000多人患病,数百人死亡。这种病毒起源于非洲的乌干达,是通过蚊子跟着人类上了飞机,传到大洋彼岸的美国及全世界。有些看似遥不可及的疾病会随着人的流动而迅速传播。人类环境的变化也会迫使病毒为了生存而被动适应,环境变化非常快,带动了病毒变异加快。有些变异并不引起人类的疾病,但有的变异就会导致严重的疾病。我们不要去破坏大自然的循环,最残忍的行为就是吃野生动物,很有可能埋下病毒流行的隐患。 其实冠状病毒有多种,很多野生动物都携带冠状病毒。我建议今后我们要像监测流感病毒那样监测冠状病毒,定期监测它们有没有变异、“作怪”的倾向。 我相信中国研制的疫苗不会晚于外国 ●中国的病毒研究水平我不敢说引领世界,但可以说处于国际先进水平。在结构病毒学的研究方面我们是国际领先的。 ●从实验室找到抗体到真正应用到病人身上需要一些时间,但这个过程不会很长。 解放日报:新型冠状病毒已经蔓延至多个国家,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对于这样的公共卫生事件,有没有全球联动的应对机制? 闻玉梅:全球联动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流感,由于流感病毒高度的易变性和不可确定性,为了疫苗更有效,流感疫苗中所含病毒组分需要定期替换。每年全世界各个国家都会把流感病毒的毒株送到世界卫生组织去,我们中国也会提供。世卫组织会在南、北半球各组织一次流感疫苗会议,就下一个流感季节流感疫苗的构成提出建议。现在有些科学家还在研究能覆盖所有种类流感的疫苗。 解放日报:目前中国的病毒研究水平在国际上处于怎样的位置? 闻玉梅:中国的病毒研究水平我不敢说引领世界,但可以说处于国际先进水平。这次我们国家的科研人员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分离出病毒株、找到诊断的方法、筛选出一些药物,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此外,在结构病毒学的研究方面我们是国际领先的。 解放日报:据您所知,抑制新型冠状病毒的疫苗研究进展如何,何时有望问世? 闻玉梅:现在全国的科研机构都在努力,疫苗研发的速度取决于采用什么样的技术。疫苗是给正常人使用的,除了关注它的有效性,安全性也很重要,必须经过一套严格的临床考核程序。所以,疫苗从研制成功,到用到人身上是有一个过程的。不过,我相信中国研制的疫苗不会晚于外国。 疫苗主要用于预防,在关注疫苗的同时,我们也要研究相关抗体的性质与功能,中和抗体对重症病人的救治可能有重要的作用。我们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医学分子病毒学重点实验室已经找到了一些有价值的抗体,正在进一步分析其功能。我相信其他实验室也有成果。和疫苗相似的是,从实验室找到抗体到真正应用到病人身上也需要一些时间,但这个过程不会很长。 解放日报:有报道说,美国目前有一款药物可能对新型冠状病毒病人有效,您怎么看? 闻玉梅:就发表的论文数据来看,这款药用在那位病人身上是有效的,但对一个人有效不足以说明问题,还需要有更多的病例进行验证。我们期待会有好的疗效,但还是要用严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 人物 “我不挂帅谁挂帅” 小时候的梦想是学唱戏 闻玉梅出生于北京,成长于上海,却与湖北有着割不断的渊源。她的祖籍在湖北浠水,父亲闻亦传是著名爱国诗人闻一多的堂兄。 闻玉梅的父母是近代中国最早一批的留美博士。父亲闻亦传回国后任北京协和医学院解剖系副教授,母亲桂质良是我国第一位女性精神病学、儿童精神病学和心理卫生专家。 出生于医生之家的闻玉梅,小时候的梦想是学唱戏。 母亲得知后,并未强加阻拦,她用自己的经验告诉女儿:喜欢一件事,并不代表就适合从事这个职业。最终,闻玉梅和姐姐都走上了医学的道路。 从原上海医学院毕业后,闻玉梅投入了微生物学与免疫学的研究。曾有人问她,为什么在众多医学领域中选择最枯燥的分子病毒学?闻玉梅的回答是:研究病毒看似寂寞,实则变化莫测,永远充满着未知,而且它还关系着无数人的生命健康。 把病人的眼泪滴到自己眼里做试验 1971年,红眼病在全国大规模流行。由于致病原因一度不明,患者大量使用抗生素滴眼进行治疗。为了在最短时间内找出红眼病的“真凶”,闻玉梅和另一位医生决定,把病人的眼泪经过除菌过滤后滴到自己的眼睛里做试验。 试验开始前,闻玉梅与其他医生约定:“一旦我们发病,马上把我们隔离,不要传染给其他人。” 两天后,闻玉梅果然染上了红眼病。试验结果证明,引起红眼病的并非细菌,而是病毒。全国的患者不必再白白浪费抗生素,只需要用生理盐水进行洗眼就能治疗。 1988年,闻玉梅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开展“复合型治疗性乙肝病毒疫苗”的研发。仅仅动物模型试验,她就和团队一起做了14年。她甚至把疫苗往自己身上注射做试验。 非典肆虐时,她赶到广州研制灭活SARS病毒的免疫预防滴鼻剂。许多人劝闻玉梅,不必亲自进实验室,她却坚持:“这里面有第一手资料,我怎么能不去!?”在被称为“魔鬼实验室”的P3实验室里,她与学生将SARS病毒株培养出大量用于实验的病毒液,他们每天接触大量的活病毒,最多时每毫升就高达1亿个病毒。 回沪后,在隔离的日子里,闻玉梅不忘用电话和电子邮件跟学生联系,指导学生的学业。50多年来,她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培养了几十届学生,其中有不少人成了所在领域的学科带头人,为中国的科研事业贡献力量。 2014年初,80岁的闻玉梅为复旦学子开设了一门看似与她的研究领域无关的新课程:人文医学导论。这门由闻玉梅携手解剖学专家彭裕文、哲学家俞吾金一起开设的课程,不仅吸引了医学生,也吸引了法学院、经济学院、新闻学院的学生。最初20人的小班课在学生们的呼吁下,被打造成了一堂网络共享课,全国400多所高校十余万名学生参与了学习。 “这是一场硬仗,需要我们携手作战” 上中学时,闻玉梅的同班同学李世济和她一样喜爱京剧,也考上了医学院,最终却放弃学医,专攻程派青衣,后来成了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与病毒打了一辈子交道的闻玉梅一直没有放弃唱戏的爱好。如今,她最喜欢的戏是《穆桂英挂帅》,她常用戏里的那句“我不挂帅谁挂帅,我不领兵谁领兵”来勉励自己。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初起之时,闻玉梅就发表了一篇相关的研究论文,并提出了一系列防控建议。她打电话给上海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教授:“你写一篇文章呼吁一下,防疫有其自身规律,目前需要的是理性科学对待。”张文宏当天晚上就写下了《恐慌与激情过后,该如何冷静思考我们的未来抗击新冠之路》,发人深省。 疫情当前,闻玉梅还与汤钊猷、邱蔚六、戴尅戎等11位院士联合向上海市民发出了一份倡议书。倡议书上这样写道:“这是一次考验,需要我们并肩承受;这是一场硬仗,需要我们携手作战。在一切疾病与困厄面前,我们都是命运共同体,医患同心、全民同行,守护健康、敬畏自然、珍爱生命,为这座卓越的城市书写传奇,在这个崭新的时代创造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