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锐作家网络聊天实录(2006年6月28日14:00——15:00)
作家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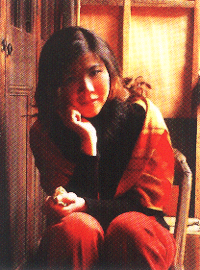
薛舒,女。从事旅游专业教学工作,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2002年开始发表小说,上海市作家协会新世纪第一届青年创作班学员,处女作短篇小说《记忆刘湾》,发表于《收获》2002年第五期,受到王安忆等人的称道。

于东田,1977年6月出生于北京,现为上海戏剧学院电视艺术学院教师。1997年开始写小说,著有长篇小说《大路千条》,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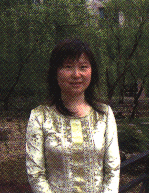
滕肖斓,女。1976年生于上海,2001年起写作,至今发表中短篇小说约六十余万字。小说多次被转载。

任晓雯,女。1999年开始写作,小说见于《人民文学》、《钟山》、《上海文学》、《天涯》、《大家》、《长城》等文学期刊。
夜X,真名陶磊。萌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1999
)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2003年加入上海市作协青年创作班,首届《上海文学》全国新人文学奖小说入围奖。
聊天实录:
麦穗奇(主持人):“上海新锐作家文库”首辑五种是上海市作家协会和上海文艺出版社联手推出的上海青年作家薛舒、任晓雯、于东田、滕肖澜、陶磊(夜x)的中短篇小说精选集。6月19日,由上海市作家协会、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联合主办的“上海新锐作家创作研讨会暨新书首发式”在上海师范大学举行。今天我们在文学会馆网站上召开新锐作家的作品讨论,意在进一步对作家的作品进行探讨。
麦穗奇:今天我们邀请了作家本人,包括部分评论家。下面我们就分别请他们发言。
网友(天真与经验):我来提个问题。我很奇怪,于东田年纪轻轻,为什么会在小说中写那些很久以前的事?和其他的年轻作家所关注的问题不同,请谈谈你这方面的想法。很好奇!
于东田:小说的本质是虚构,写过去、写未来,其实都是写现实。
网友(qz):您总是写一些抗战和革命的故事,是因为从小有这样的情结、情怀还是身边都是故事中的人?
于东田:战争时期是最能体现一个民族的特点,有非常好的人物和人物关系可以写,所以我就比较喜欢写这样的题材。
网友(巴巴):我看了任晓雯的几个小说,觉得在目前的年轻作家里是很有潜力的一位,而且是为数不多的可以在纯文学范畴里探讨的作家,并且还是个美女呢,很难得的,希望你可以保持这个状态,写出更好的作品。
任晓雯:谢谢!
麦穗奇(主持人):先请费爱能就新税作家的作品谈点自己的看法。
费爱能:不久前,作家协会和上海文艺出版社以及上师大人文学院一起召开五位新锐作家的研讨会,会上有上海的著名评论家王洪生、杨健龙等七八位评论家做了精彩的发言。他们一致肯定了这五位作家的创作,代表了上海当今青年作家文学写作的主流。五位作家都是上海作协新世纪首届青年创作讲学班的学员,在他们的创作上,有传统的传承,也有所谓八0后青年写作的锐气,有着自己的读者群。我们希望通过这次网上聊天研讨,更好地促进青年的文学写作。
网友(qz):《连襟》写成对话的形式是为了更好体现题目?乍读让人觉得是中国语境的等待戈多。
于东田:《连襟》是一个剧本的初稿,所以写成了对话的形式。
网友(小雨):任晓雯:我很喜欢你对悲悯与讽刺的看法。我同意悲悯比讽刺更高。但是很多人经常把悲悯理解为讽刺,不知道你遇没遇到过这种情况?还有你可不可以进一步区分一下二者?
任晓雯:讽刺提供了某种价值判断,而悲鸣把判断的权利留给了读者。具体的区分可以见我的文章。
网友(天真与经验):于东田,你的作品关注民族的历史,其中有对历史的思考。很发人深省。你写这些题材,意图不仅仅是要记取历史,还要重新审视历史,是吗?请谈谈你的进一步想法。还有,你的作品写的很好,喜欢看。
于东田:谢谢您。小说是各种可能性的历史。
网友(蝴蝶):我是为退休军官,就驻在薛老师工作的地方,多年前就认得了。6月15日在当地图书馆书友会上又见了您。我提问的问题是:——你心中的军人和你刻画的军人之间的距离。请直说。
薛舒:退休军官问我在我的眼里,现实中的军人和作品中的军人有什么不同.我写过几个小说中出现军人,就是《寻找雅葛布》,还有是《麦粒肿》中的军医.其实在我的眼里军人始终也是普通人.并不是要把雅葛布当作一个军人的形象去刻画,而是要写一位少年,责任心,英雄气质,但又渺小的少年.和军人无多大关系,如果他只是一个放羊的,也许也一样。
网友(qz):您说故事就像平时说话,是从写作一开始就不喜欢修饰么?
于东田:不一样的故事,有不一样的写法。我觉得我写的故事就应该是现在这样的写法。
网友(蚊子的粉丝):任晓雯:关注你的小说很久了,觉得你的文字非常好,简洁大气有节奏感,小说的紧张度也控制的很好,据说您先生也是一位小说家,两个作家在一起是否对创作有裨益呢?
任晓雯:谢谢夸奖。作家在一起对创作是会有益的,前提是双方的个性都不是十分尖锐。
网友(卡夫卡):注意到任晓雯作品里对人性和人文的感悟,你觉得你们年轻一代对此的感悟相比上一代作家区别在哪里?
任晓雯:上一代作家经历了只有集体语言,没有个人语言的时代,而这代作家,他也许在他写作最初的时候只有自我。也许双方是从各自的出发点分享共同的目的,但他们的途径不同,必然会导致有所区别。
网友(孤雁):作家所写的作品是怎样构思出来的,我写了几部小说,朋友们看了都说犯困。我想听听你是怎么写出那么好的作品的?
薛舒:我不知道别人的经验是怎样的,但我自己的写作任何一个作品时,灵感的火花也许只是很小的一个触碰.比如看到很古老的理发店里很红粉的男理发师,于是写一个《小乔剃头店》哈哈------比如听到有人在常蒙古长调,声音苍老,于是写一个《图勒漠的怀抱》.比如朋友离婚,就想到要写《破碎的花瓶》。
网友(小雨):文化经济学解释为什么很多人挤在创造性的行当(比如说小说创作)即使做不了superstar也留连不去。两种答案比较常见:1,锦标赛模型,意思是说选手们觉得自己能成功,需要的是时间和机会。2。为艺术而艺术模型,意思是选手们虽然知道成功也许无望,但是就乐意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不管哪一种,这些人都选择留下来,而不是去找一份全职的好一点的工作。但是理论总是简单化。有没有第三种,第四种可能性,比如说这些人做别的更做不来,在这里耗着还算有点面子。请问各位新锐作家,你们怎么看待自己在社会上的位置。如果您觉得我的话有刻薄的地方,那是因为我对作家有求比较高,觉得她们不会很计较凡俗的面子事儿。
夜x:我觉得对每一个写作者来说,可能平时都会认为自己是锦标赛模型,而在遭遇一定挫折之后,恐怕免不了会自己“为艺术而艺术模型”来安慰自己。但正如你所说的,理论是简单化,模型也是简单化,应该不会有三四种可能,而是自己有自己的可能。我不太清楚其他作者是怎样处理这种矛盾的,而我个人比较欣赏的态度是,把创作当作是归于精神创作的范畴,与日常的谋生和社会的位置分开来。
网友(卡夫卡):任晓雯同学,我是你复旦同窗,没想到你这个研究生没研究新闻,却去研究小说了,想问除了创作外,你平时还干点别的什么?
任晓雯:我平时在一个叫“普茶客”的茶叶公司上班,专门经销高档普洱茶。
网友(qz):怎么想到用男性的“我”来写《遗忘之后》这样一篇小说?
于东田:我的很多小说都是用男性的我来写。
麦穗奇:下面请张重光谈谈对这些青年作家作品的看法。张重光是一个文学老编辑了,几十年浸润在文学中,应该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和见解了。
张重光(《上海文学》编辑):我作为一个老编辑,很高兴能看法这些新锐作家的作品,其中有个人我还是他的责任编辑。我觉得他们的出现是带给了新一代作家正在走向成熟,比如说像薛舒,看到她的作品我就想到了彭瑞高,一位写上海农村题材的作家。在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彭瑞高,现在薛舒在这方面的风格也是比较明显的,她给我们所刻划的这种场景,带着很明显的上海郊县的,或者说金山地区的特征。她善于编故事、讲故事,而且脱离了一种单纯的自我,能够跳开自我的创作,而且显得比较成熟。
和她创作风格比较接近的滕肖斓,她的作品跟她的人给人的感觉是很吻合的感觉,是比较朴素,比较沉稳,故事的框架都搭得比较大气,文字的叙述相当朴素。任晓雯她的作品,尤其她的《飞毯》、《乐鹏程二三事》给我一种我要重新思考对文学作品,在我本来的观念里,我曾经写过一篇是《细腻、细腻再细腻》,就是把人物内心最复杂的东西表现出现。但是她的手法就是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而且这种简单化我觉得又是有相当的力度,她的人物并不是因此而显得粗糙,同样发人深思,这好像对我们搞创作的人说起来有很大的启示。
夜X我觉得他是这几个人里面科技含量最高的一个,比如说他的《奈特鲁尼克》,我曾经是他小说《寻找》的责任编辑,我看他的作品有一种很兴奋的感觉,这种兴奋是我要不断的思索,要不断的动脑筋,这也是对自己思想的一种开发,可以想到很多东西,不是像人家的作品可以一览无余的感觉,他是需要你去思索,不是一般化的问题。
还有于东田,她在我们上海文学发过不少作品,起码有五部作品。在我没看到她以前,我觉得那种感觉就是像在看那种生活底子相当厚实的、而且那种经历是一般人、尤其像我们上海地区的人所难以经历的生活,她所驾驭的革命题材气势比较大,但是她又不是一种说教,我觉得她的作品里面在气势很大的作品里面也蕴藏着一种幽默,一种内在的、会心的东西在里面。而且我觉得她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画面感很强,刚才有读者问到是不是可以改成电影,我觉得像《狗不是狼》就可以改成电影,画面感很强。我们期待她有更好的如《红高梁》这样的作品能够问世。总的看起来,我觉得这五位新锐作家好象还可以,跟一些已经有些成就的,如唐颖、潘向黎、殷惠芬、徐惠照,我觉得他们这几位似乎还存在一定的距离,尽管在表现手法上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在一种生活的厚度,还有就是一种阅读的快感,对于人物内心的一种相当细腻的把握,我觉得还存在一定的距离。但是我相信这种距离并不是很遥远的。
网友(阿小):薛舒的都市小说和小镇小说区别特别大,几乎不象同一个人写出来的,请薛舒回答一下创作时的想法好吗?
薛舒:我是出生和成长在一个交替年代中的人,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贯穿小镇的流水故事,长大后的生活完全进入城市,这又与小镇有着渊源,同时也割裂。我自己更喜欢我的小镇故事系列,因为这是沉淀更深沉的一部分生活,也是更有意味的生活。而城市情感系列那些,我觉得,也许十年后再来写,我会写得很成熟一些吧。
李洪华(上海师大人文学院博士生):
在欲望裹挟下的庸俗和颓废日益在都市里生长在市场上畅销在文学中弥漫的今天,上海新锐作家薛舒持守着一份清纯而严肃的文学情怀,打量繁华都市的远近内外,用一种年少而老成的笔调把都市少女的早春情怀点染得疏密有致,把市郊小镇的常人往事铺叙得委婉动人。那感性描写的细腻和知性思辨的绵密所形成的张力共同造就了薛舒叙事语言的魅力。这种成熟的魅力似乎让人很难与她的实际写作年龄产生联想。
发表于2002年第四期《收获》上的处女作《记忆刘湾》,标志着薛舒“市郊小镇系列”高起点的开端。作者把一段具有长篇架构的小镇历史纳入到精制的短篇部局中,用一种轻松活泼而又略带忧伤的笔调叙述了几个刘湾人物略显风流、略带沧桑的生活往事。
陈思和说:薛舒的作品最难得的是洗净了这个混乱时代强加给一代人难免有的焦虑和浮躁,她用从容不迫的笔调写出了自己记忆中的江南农村历史的变动,又因身处上海的郊区,那个庞大怪物的巨变不能不影响着她的身边生活的深刻变化。薛舒笔下的刘湾虽然也经历过政治风云的剥蚀,但是她总是让乱离的时代风云退居到极远的淡处作为一种潜隐的背景存在。薛舒的“刘湾”系列在市郊小镇的风情画卷中开辟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园地”,这一风格从第一篇《记忆刘湾》开始便初露端倪,愈往后来更见成熟。
薛舒的“都市女性”系列隐含着“走入上海”和“走出上海”两种叙事结构。在《破碎的花瓶》、《纸牡丹》、《遭遇爱情的鸟》、《一片花两片花》、《流浪的蒲公英》等作品中,作者走入单身女性公寓、大众钢琴酒吧、虚拟网络世界、江边轮渡码头以及弄堂里的石库门旧宅等上海大都市的内里,用纤细的笔触勾勒出都市女性纷乱繁复的情爱心理。而《图勒漠的怀抱》、《寻找雅各布》、《独行天下》等作品,虽然讲述的仍是都市女性的情感故事,但作者已然走出喧嚣的都市投身于高原大漠和藏歌羌笛,把都市女性的细腻柔情置放在高原大漠的豪迈奔放和藏歌羌笛的凄楚迷离中,烛照出都市女性不一般的坚定和执著。作者在绮丽的自然景观和迷离的藏族风情的纪游中穿插着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的都市情感纠葛。完全超越了过去都市对乡土眺望和想象的传统视角,她同笔下的主人公一道走出都市投入远离尘嚣的大自然,亲历着一次又一次的精神探索和心灵悸动。她的这类小说在都市——自然——都市的叙事结构中隐喻着都市对家园的精神怀想。这一独特的叙事结构实际上开启了都市写作的新路向。
网友(我是呱):于东田:比起上一本《大路千条》,这本书的封面要好看许多哈!请问这应该是您出版的第二本书,较前一本心态上有什么不同?有什么新的感觉和感受呢?
于东田:出书非常高兴,感谢作协、感谢文艺出版社、感谢上海文学。
网友(小雨):谢谢你的答复。我的理解略有不同,悲悯是对人性的不圆满的咏叹,包括讽刺者自身。第二个问题:你的小说很有深度,也很好读。请问你怎么权衡真诚的写作(如果有这种东西存在的话)和商业化的尝试?
任晓雯:所谓的真诚写作和商业化的尝试,两者没有兼容。因为商业化写作本身是一种技术含量很高的、有难度的工作,它和纯文学写作(也许就是你所说的真诚写作),虽然都是写作,但其实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
网友(风满楼):晓雯妹妹,我读过你不少小说,可是还是最喜欢你早期的作品未完成的短篇。也许因为你在那里面表达了较多的情感。不知道你以后会不会还会再写类似的作品。
任晓雯:在我后来的作品中,也有很多情感,但我学会了控制力。
杨剑龙(上师大教授):
任晓雯的小说描述的并非一个纯情世界,而是充满着复杂与混乱的世界,她的笔下几乎没有温文尔雅含情脉脉的恋情,有的只是直截了当的欲望发泄;她的笔下几乎没有相濡以沫一往情深的真情,有的只是相互利用的男女关系。任晓雯的笔下呈现出的是一个复杂与混乱的世界,大多为底层社会的窘困人生,渔民、小贩、妓女、拾荒者、发廊女、车间主任、长途司机、痴呆儿、绑架者、贩毒者,成为她小说描绘的主要对象。
任晓雯是一位诗人,也是一位小说家,她受到西方现代派小说的影响,她以一种诗歌跳跃的笔触叙写小说,在小说叙事中她在模仿中有所创造,她常常让多个叙述者在一个时间里同时发声,使各种叙述元素碰撞出一种复杂甚至混乱的美。
在小说创作中,任晓雯虽然过于执著于现代社会中畸形性关系的关注,孜孜于对死亡母体的描写,小说灵动有余而厚实不够,在叙事呈现出复杂甚至混乱的美中,常常阻碍了阅读的顺畅,但是其小说创作延续了新时期以来形式探索的脉络,在新世纪以来小说创作回归写实的潮流中,呈现出其独特的努力与价值。
滕肖澜的小说大多为一个个曲折的悲情故事,她讲述的多为人世间执著追求却并不如意的情爱人生,在对于社会诸多弱势群体生活的描述中,塑造了不少颇具个性的人物形象,以颇为流畅细腻的写实笔触,建构其小说悲婉写实的风格。她强调“小说应该是悲天悯人的……应该有一点责任感,把目光放远放宽,关注弱势群体,关注广大老百姓,用笔勾勒出一个现实生活”(滕肖澜《十朵玫瑰·后记》)。
滕肖澜小说起点较高,其处女作《梦里的老鼠》就显示出创作实力。在短短几年的创作中,其小说已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在对于弱势群体生活与情感的描写中,具有悲天悯人的意味。倘若克服年轻女性形象的类同化、拓宽小说的叙事手法,滕肖澜的小说创作会拓展出一个新的天地。
网友(乱了感觉):我怎样才可以将自己的诗歌出版出来啊?
费爱能:请带着你的诗集,到上海作家协会文学创作中心。
杨中举(上师大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生,副教授):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新锐作家系列作品,意欲提供上海文学创作的前沿概貌,实为功德之举。名之为“新锐”,自当有其作者的新、内容的新、手法的新,也当有其思想的锐利、艺术风格的前卫和读者接受时的凌利与切透感。这当然要时间与读者的阅读接受来检验。
我认为对五位作家,特别是对任晓雯、夜X的创作进行解读必须从中西方两大小说传统背景为基础进行才能够把他们定位好,尤其是把握其“新锐”的真面目,绝不能忽视这批作家的西方文学功底,也就是说,西方小说传统应当成为我们审视与把握新锐作家创作的重要文学参照系统。稍有西方文学知识的人都会看到他们对西方文学有意无意中的借鉴与学习。再换言之,解读这些小说,不结合西方小说,无异于隔靴搔痒。任晓雯是一个有着较好中西方文学功底的年轻作家;想象力丰富,行文间透着一种灵气与自信。对西方文学艺术的借鉴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对任晓雯总的印象是有才气,但也有不少值得反思的地方,一个有创作潜力的作家其不足往往也是非常明显的,我没有来得及读完其全部作品,没能做理论与理性的分析,只是印象式的点评,有偏见之处,请指正。
麦穗奇(主持人):今天大家发言畅所欲言,网上也有很多朋友上来提问和发言。今天的活动就到此结束,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