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吴正(2006年3月8日14:00——15:00)文学聊天实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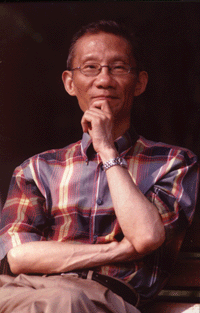
麦穗奇(主持人):今天我们邀请的嘉宾吴正先生是从小生活在上海,改革开放后赴香港定居的著名作家。在我们的材料介绍中,也可以看到吴正先生始终坚持认为自己是上海作家,而不是香港作家。因此,我们今天邀请吴正先生来这里聊天,是对吴正先生作为上海作家的一个认可。吴先生最近出版了一本新书《长夜半生》(国内版)(下同),我们今天想就这本新书,以及吴正先生的创作生涯,进行一些访谈和交流,同时也欢迎网上的一些朋友提出自己的意见和问题。
麦穗奇:我们先请吴正先生先简单地作个自我介绍。
吴正(嘉宾):我认为主要介绍一下自己的创作生涯,这个道路对我来说是很崎岖的,1978年改革开放我放开上海去香港,那时候中国大陆还是文革的尾声,我从生出来到青年时代一时在上海,那个时期我已经在创作了,但这作品不能拿出来,这是我的第一个阶段。我因为太喜欢文学,是自然而发的,而且也没有地方发表。到了香港以后,完全进入另一个世界,政治的枷锁没有了,经济的枷锁就出来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到了香港以后还是不能从事自己所喜爱的文学。可见,要从事自己所喜爱的事情是很难的。到了香港以后,我要掌握好父亲的生意,先要搞定生活的状态。
吴正:到了香港之后的五年没有碰过书,并且适应了那里的情况,但到了后来慢慢又碰上了书,1984年开始先在国内试刊,还在一些大型的文学杂志上发表文章,真正使我走上文学道路的、成为半专家作家的是长篇小说《上海人》。以后就陆续出版了各种版本在内的大概有25部左右的作品。
吴正:到了自己五十几岁以后,所谓五十知天命,我自己生存的经济条件具备了,我就全部转向文学创作,这时候我对自己的定位就是专家作家。这期间有各种出版社出版我的东西,国内主要有人民文学出版社,一部是长篇小说《上海人》,另一部是《吴正诗选》;另外还有上海文艺出版社也出了两本,一本书《诗集》,一本是《随笔》。其他的出版社包括花城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学林出版社、时代文艺出版社等等。香港有几家出版社,最近出版的《长夜半生》(国内版)(另一名为立交人生——海外版),还有《小说,小说》是由香港的日月出版社出版的;台湾的希代出版社也出版过我的作品。
麦穗奇:吴先生,据我所知,你原来一开始仅仅是诗歌创作,是什么启发你走上小说创作的道路?而诗歌和小说的写作风格有很大区别,你是怎么完成这个转变的?因为我感觉在你的小说中,还能感受到文字非常精美、简练的风格。
吴正:诗歌创作并不是我一个人这样做的,很多作家都是从诗歌创作开始他们的文学生涯的。这是因为同一个人的生理、心理成长有关。我们年青的时候对诗歌都会有一种冲动,而且会对古今中外的大诗人极其崇拜,这样就会有一个模仿,诗歌创作就开始了。但到了一定的阶段,很多人写了一部分诗歌后就不会再有文学创作;但是有一部分人继续创作,这就是作家概念上的诗人;但也有一部分写诗的作家会转变,他会写小说,因为小说的涵盖度太大。我始终讲到一句话:少年诗歌,中年小说,老年散文。这很合乎一个人的生理缺陷。所以用诗歌的形式转化成小说,其中的难度主要是语言思维上的难度比较大。但是我觉得一旦转化成功,这样的作家就比较会在语言的表达上更有特色、更有味道。
吴正:一旦进入小说创作以后,尤其是从诗歌这种意向思维进入的小说创作的时候,你就会对小说创作着迷,整个人都陷进去,有时候是不能自拔,所以现在我基本是小说创作的感觉特别强,至少在最近这段时间内。
麦穗奇:你的这本新书的小说我已经看过,在这部小说中有许多方面是保持了过去写实主义的风格,也有很多是一种意识流式的写作风格,非常虚幻,完全是一种流动的思维。我想请问吴正先生,你是怎样处理虚实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怎样妥善把握虚幻与写实?
吴正:我的第一部长篇《上海人》,有33万字,也拍成了连续剧,这一部作品是完全写实主义的。这时候在我的头脑中还不能完全排除青少年时期所看的所有的写实主义大师们的作品给我的影响。所以就然而然地就写了一部纯写实主义的作品《上海人》。但是在我第二部长篇的时候产生了很大形式上的变化,这不是故意追求的,其实追求也追求不到,他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这种变化。什么道理?就是讲写诗的元素走进了小说中,这是一条。第二条,生活告诉了我,写实不见得是小说表达的最好形态。
我可以讲这样一句话,如果你用一百万字(我的数字概念)的写实主义,如果用意识流或者类意识流的创作方式(我现在的小说也不见得是意识流,我也不能很准确地给它定位),可能三十万字就可以达到一百万字的效果。什么道理呢?因为这七十万字的片幅是由读者被激发出来的想像填补进去的,因为读者也需要用他的想像与作者保持创作互动,这是一个作家创作的最好效果。因为作家的目的是用他的一个思维激活读者的一串思维,如果达到这样的效果的话,我们就产生了原子核爆的文学能量。所以,我的创作会自然而然地走上这条道路,而且是与我的诗歌创作的思维习惯分不开的。
麦穗奇:看你的作品我还有一个印象,你的作品中间不少地方写到了性,但是你作品中很多性的描写完全不同于我们现在当前市场上热销的作品,显得非常的干净,又很含蓄,却又表达了作者希望表达的意境,你是怎么处理作品中性的描写,包括性和文学的关系?
吴正:我觉得性与文学是这样的,人生离不开性,文学素材因为也离不开性素材。这里有两条:文学与性的关系是将文学纳入性呢,还是将性纳入文学?仅一个选择意念上毫厘之差便造成了一部作品存在价值上永恒可否的千里之别;男女之爱需要性,但用性作为诱饵来垂钓男人的女人是无耻的,更是可怜的。这只能说明一个已失去了内在人格魅力的女人的孤注一掷和“奋不顾身”的绝望。文学创作中也少不了写性,但以纯性描写作为题材来吸引读者的作者同样是可耻与劣等的,这正好招供了作家对文学这门艺术的追求已再无所作为以及无能为力了的这一桩事实。
吴正:还有一个写性有一个特点:一个中青年作者写性的方式往往是投入和身临其境,而一个老年作家写性却明显是带上了一种觉悟者的清醒,缺乏热烈,但理性有余。对人生已失去了“性”趣,隔着时空的禁区对性进行考量是一种资格和姿态,站在记忆的美丽的彩虹桥上,向人世间投以俯瞰。为什么要这样写,这是我在文学中写到性素材的时候的理念是什么。
麦穗奇:现在网上有些朋友提了一些问题,接下来请吴正先生回答网上朋友提出的问题。
网友:听说您的《立交人生》现在有大陆版的了,是由哪家出版社出版的?为什么要改名叫《长夜半生》呢,有什么寓意?
吴正:《立交人生》的大陆版的名字就叫《长夜半生》,是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立交人生》的寓意是因为每一个人的人生就如立交桥一样,互相不能沟通,也就如你在立交桥上看到下面开过一辆车,你却不能往下跳的道理是一致的,很近但却没有用,是隔离的,这就是《立交人生》的寓意。至于《长夜半生》的寓意,这里面有两个A、B主角(是同一个人的两个面)分别不同在上海的一条马路(淮海路)和在香港的一条马路同时同步在行进,从黄昏走到黎明来临之际,这是这部小说的一条线,这两个人通过交叉重叠的想像与意识的交流,将他们的大半生的事、遭遇、感受全写在了小说中,所以名字就叫《长夜半生》。另外这部小说的英文版是取了两个名字,一是《one
night as long as a lifetime》,另一个是《interwoven》(中文名是编织的意思)。
网友:您觉得《长夜半生》最能打动读者的是什么?
吴正:我曾经跟读者谈起,很多读者反映,这部书初读时不太易进入,但一旦进入,就觉得很有味道,趣味无穷。其中有一个时代叫“千结衫”,那时候中国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物质极度溃乏的年代(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因为其中的表哥要到崇明岛去务实,他表妹送给他一件毛衣,但是没有钱买,那时候有废品商店,在那里买了一大堆的绒线头,用编辫子的方式编成一条一条的长绒线,再用这个绒线为她的表哥织了一件毛衣,因为是编织的关系,在衣服上留下了大量的线头,后来这个表哥当了作家,跟随上海的某个作家代表团去参加法国的一个文化节,他在蓬皮杜现代艺术馆看到了一件现代艺术展品,法国艺术家居然也是用这么多的线头织了一件毛衣,你想,在我们的时代,就有这种现代作品,这是一种多大的反差,但显然他的表妹不会去做一件现代的艺术作品。可见,不管是现代艺术展品,还是现代时代要用的日用品,其中的人性含量是一致的。
网友:tina:I want to support my father for being on this
forum.
吴正:Tina,I have read your question.thank you for supporting
me!I will try my best.
网友:char:I am here to support my father. I am so proud of
you.
吴正:CHARMAINE.I thank too,you supporting my writing,this is
just what I want,thank again.
麦穗奇:吴先生,我注意到你有时在上海,有时候是在香港,两地来回走动。这样的一种生活背景,包括你本身又承担一份生意上的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怎样调整自己的关系,如何协调好自己生意和写作的关系?尤其是在两个大城市的文化背景,以你的创作带来怎样的影响?你的思维会不会因为身居两地而经常被打断,包括你的写作怎样适应经常在两地经常走动的这种环境?
吴正:关于第一个问题,生意同文学创作的协调关系,我用一句话:生意是我的生存事业,文学是我的生命事业。如果掌握好了这条原则,什么都能协调。
吴正:第二个问题,正因为我在两地时空交错的飞来飞去,让我经常有一种往返于不同空间、不同文化背景,以及最重要的是有不同时间段的感觉,因此所谓意识流或者类意识流创作的模式就会出现。刚刚主持人讲的这个问题确实很有意识,我回到香港,那一头的生活又接上了;然后我回来上海,这一头的生活继续接上。你设想,一个人做梦白天醒来,白天干他的事,晚上做他的梦。但是我们的梦是片断的,如果梦也是能续上的话,我们不是在白天做一回事,晚上又做另一回事吗?我现在就是这种感觉,所以在我的《长夜半夜》中,这种感觉很强很强,这也是同我的特殊生存模式有关的。
麦穗奇:你的这本新的作品,我有幸拜读了。我感受到你的这部作品在其结构上有其非常独特的风格,在其表现手法上也有自己独到和创新的思考。我在阅读你的作品中,有很多地方受到细节描写出影响,把自己带到那里,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常常使我阅读作品的同时感受作者所要表达的心声,体验作品中人物内心的思考和感情。类似这些感受,不知道你是否有意地进行了这方面的探索?
吴正:这一部书的结构确实是很独特,我自己也承认。其实我在写的时候,并没有刻意追究独特的结构,就觉得需要某种交错的时空表达方式来表达某一个故事。因为我们生活在现代,尤其是我们这代人,从我们革命化的时期生活到今天,本身就有一个时空错位感时刻在困扰着我们,不是困扰着我一个人,是困扰着我们整整一代人。每个人仔细理一理,都有不知道今天是在梦里,以前的岁月是现实,还是以前在梦里,今天的生活是现实的感觉。这一种现实与梦幻的犬牙交错的感觉,正是我觉得我要表达我们这代人、这50年当代中国生活的最好形式。
吴正:我再加一句,我们在三十年以前,最憎恨、最反对、最厌恶的东西,正是我们现在最追求、最崇拜、最欣赏的东西。这样的反差,试问在中国历史上,或者在世界历史上哪一代人能够在一生中同时遇到。所以从这一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这一代人是很幸运的一代人。我刚刚回答主持人的看法,一个创作的形式绝对不是你有意要去做而能成功的,还是这句老话,为你需要创作的内容服务。这就像一件衣服度身定做,还是你去衣服店买一件大、中、小,或者超大号的衣裳穿在身上,是一个道理。至于讲对上海的场景细节,在我的头脑中已经像墨刻一样地深深地印刻上了,所以在我所有的作品中,它们会不期而然地流露出来。
吴正:就如网上有位网友提到说,上海与香港,对你而言是怎样的情结?上海,尤其是童年、青少年的上海,他的记忆是同我的生命同在的,永远也不会有丝毫淡化的可能。所以在所有的文学创作中都会有他的流露。所以在澳洲的一次关于我作品的专业研讨会上,很多人提了这是意识流作品,也有人说了这是中国最新的结构主义作品,或者说是表现主义作品。其实这些作品如何定位,是如何一回事,作为作家的我的心中无数,我只知道怎么写最能表达我,如此而已。
麦穗奇: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聊天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吴正先生,因为我们事先安排今天,非常不凑巧的是,吴正先生原本还在香港,吴正先生为了这次的对话活动,他前天晚上特意从香港飞回来,过后还要赶回去。因此,在结束之前,真诚地谢谢吴正先生。希望他的作品能够赢得更多读者的喜欢,希望他的作品能够赢得更多读者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