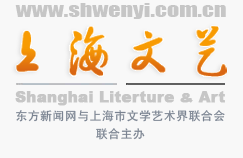中国电影事业的著名艺术大师,谢晋导演去世已经一年多了,早想写篇文章纪念他,却因一直无发抹去内心的思痛而几次都未能动笔。在谢导最后的几年里,我与谢导因一部电影而结缘并相处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是一部反映农村教育题材的电影,也是谢导从事电影事业几十年以来的一个心愿,电影的名字叫《琴桥悠悠》,我是编剧,谢导是该电影的总策划和总导演,遗憾的是谢导的突然辞世使这部电影成了他一个未了的心愿……
十年前,中国的教育问题正处于改革转型期。我因写了一部反映贫困大学生的长篇报告文学《落泪是金》和另一部长篇报告文学《中国高考报告》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我也跟着这些作品名声大振。当时有十几家大大小小的影视制作单位来找我,包括赵宝刚和中影公司这样的大腕级导演与制片单位。与谢导也是因此而结下了特殊关系。
2003年的5月,整个北京城还笼罩在非典袭击的恐怖当中,到处冷冷清清。有一天突然一位朋友打电话告诉我说:“谢晋导演要找你,想请你写一部电影本子”。我听后大为意外和激动,谢导那么著名的大导演,他会找我写本子?对方告诉我:他知道你写的几部教育题材的书影响很大,正好谢导要拍一部教育题材的电影。原来是这样!
我们第一次相见在京广大厦,我如约赶到。大楼里静悄悄的见不到一个人影。到谢导住的房间后,谢导一见如故一般地扬着他特有的大嗓门,一边笑一边指手画脚地说道:“整个楼就我一个客人!他们都害怕,我不怕!非典算个啥,我不怕!我现在住这儿是半价……”虽是第一次见面,但这位年近八十岁的老人那样乐观和爽朗的说笑,使我即刻对他产生一种特别的亲近感———谢导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对所有的人都这样平和、亲切和真诚。
坐下后谢导对我说:“建明,你的《落泪是金》一书反映当前教育问题写得非常的深刻!这样好的题材,假如不搬上银幕,作为电影人,我感到非常可惜!”
“我打算要拍一部反映农村教育题材的电影。中国的教育问题太多了。我想请你来写剧本。”谢导向我说出了他的打算。
可以这样说,我和无数中国人都是看着谢导拍的电影长大的,面对这样的一位大师的邀请,我又激动又兴奋地问他:“为什么一定要找我写这个电影呢?”
谢导笑嗬嗬地指着我:“我找你不容易啊!你是大作家,名声很大哟!我今天总算找到你了!你写的几本教育方面的书我都看了,所以找你。”我有些受宠若惊。
后来在一次朋友聚会得知,拍一部教育题材的电影谢导早有打算,他曾经打算与写过《班主任》的著名作家刘心武老师合作,后来又觉得《班主任》反映的是中国二十多年前的教育问题,与目前差异太大了,所以谢导又去找到著名作家陈祖芬老师商量,而陈祖芬老师向谢导直接推荐了我。
谢导约我写教育题材的电影,当时我心中并没有数,因为教育是个大概念,写什么呢?
谢导明确地说:“我想拍一部中国式的《山村女教师》!中国的教育我看根源是基础教育,特别是农村的教育问题,现在农村尤其是山区的孩子念不起书,考不上大学,原因就是那里的老师不行嘛!为啥老师不行?主要是那里待遇底,没有几个人立志在农村和山区教书嘛!”谢导对中国教育弊病这么一针见血,令我大为惊叹。原来他要拍一部教育题材的电影就是为这个啊!我们一老一少即刻有了共同语言。而我知道苏联的《山村女教师》是部著名的电影,谢导一生追求高品位的艺术,他的愿望就是要拍反映中国的《山村女教师》。当时我掂量了一下自己的能力,说,恐怕难以胜任。谢导立即鼓励我:“你的书写得那么好,不会有问题的。我们一起来做这件事!”有大师的话,我便鼓足了勇气。
从此,我跟着谢导断断续续地一起为这部他最后的电影开始奔波……
因为题材定位“山村女教师”,所以我们一起到了谢导的家乡熟悉情况。先到了他的老家绍兴,最后选择了温州的泰顺县作为“生活原型”基地。泰顺处于浙江与福建交界,是个偏远的山区。这个地方特别封闭,我们去的时候是从温州出发,要走四五个小时的汽车才能到达,而且一路非常不好走,是岖崎山路。那一年谢导已经是八十岁的老人了,走路常常给人感觉是摇摇晃晃的———其实他一直是这个样。但当只有我们两人时,我十分紧张,因为一旦出了事,我可担当不起———谢导是我们国宝呀!果不其然,第一次到泰顺的路上,就把我吓了一大跳,至今仍心有余悸。那一天在半道上,我们从吉普车上下来准备方便一下。坐在紧挨司机前排的他,比我先下,突然我见身材高大的谢导身子一晃,从车门口倒下,然而顺着公路边的斜坡连续翻滚了几米远……“谢导!谢导———!”我吓得飞步跑过去,迅速将他扶起。“嗯———”谢导睁开眼睛,朝我看看,又瞅瞅斜坡,若无其事地从地上直起身,说:“没事,没事,是踩空了。”
80岁的谢导真的没事。当我为他检查一遍后确定他确实没事后,长长地松了一口气,然而从此以后我常提醒自己:千万不要马虎,紧跟谢导身边。同时我也多次提醒他身边的人:务必要在他单独出门时派个人跟在他身边。“没事!我好好的要派啥人?撞手撞脚的!”谢导总是这样不听别人的劝告,非常执拗。几年后他一个在房间里去世跟身边始终没有人照料有直接关系———为这我常常感到我们许多人是对不住谢导的,他毕竟老了,八十多岁高龄的人怎么放心让他再独自走南闯北地奔波呀?
在泰顺的日子里,我负责采访和实地感受生活,谢导则忙于寻找拍摄点。晚上我们一起在宾馆里商量剧本的写作计划和电影情节的构思。这之后的近一年多时间里,我们连续三次因这部电影而到过泰顺。记得2004年春节刚过,谢导就把我带到了泰顺。从上海出发时我从苏州老家给他带去了两只老母鸡和几条阳澄湖的鲜鱼,谢导和他夫人特别高兴。在他书房里我们多次长谈,谈电影,谈社会。谢导对当时某些所谓的大片恨之入骨,道:“简直是糟塌电影!”他常常很无奈,说现在没有几个人到电影院去看电影,他认为票房价格太高,“老百姓看不起电影了,这中国电影还有啥希望?”他认为电影票应该不高于10元钱。“我就是要拍能让老百姓都看得起的电影!”大师对此耿耿于怀,但却无力扭转现实。
“中国那么多的现实主义好题材,他们在干什么?天天拍些乌七八糟的东西骗钱!糊弄老百姓!”谢导对一些所谓的名导的行为十分反感。
大师曾多次对我说,他要用最后的力量来为中国电影“正本清源”。故而,认认真真拍一部中国式的《山村女教师》成了他艺术人生中的最后一个追求和特别期待的美好愿望。然而他最终没能实现,期间的种种原因,令大师和令我都对中国当代电影界的价值取向产生了重大的疑惑和不解,这也是造成了谢导的最后一个遗憾的症结。
而作为中国电影大师的最后一个遗憾的见证者,我在与他一起的日子里学习和感受到了许多他的可贵品质,而这些宝贵的东西时常在我眼前萦绕……
我记得有一次到泰顺正是夏天,特别的热。当时我们已经对泰顺这偏远的山区产生了浓厚兴趣,谢导和我找到了“山村女教师”的故事原型和实境拍摄地。泰顺这个地方有三样东西令我和谢导激动:一是这里有许多“老房子”,这些老房子多数是明清时期那些达官贵人家留下的建筑,非常气派。难以想象在明清时期交通十分落后的年代,竟然有人将无数巨石和巨木运进深山。我和谢导对那些庭院深深的老房子喜欢得不想离去,其中我们还见到了一个村子里有两位状元留下的故居,有意思的是两位状元一文一武,那武状元家居前面,文状元家居位,一前一后,错落有致。更有别趣的是在两居之间有一条石子通道十分别致,它们由不同的两条石子路并列而成,据说为的是两位状元在同行或者对面而过一条道时相互不碰撞与躲闪。在封建社会时,状元都是有身份的人,讲究排场,在这个小山村里,一文一武的状元相处得十分和谐,堪称一绝。我和谢导对此感慨万千。泰顺的第二绝是遍布于大小山谷之间的那些美丽别致的廊桥,它们或建在悬崖之间,或建在河谷两岸,煞是壮观漂亮。我和谢导在当地百姓的引领下,几乎探秘了当地所有廊桥。泰顺的第三绝是横垣在一条条山川河谷之间的石町桥,那湍流之中忽隐忽现的一根根插入河底的石桩排列在一起,或十几米长,或几十米长,记得有条石町桥长达260多米,壮观美丽,气势磅礴。这石町桥的石柱,远远看去就像横在河谷上的一台钢琴的琴键……“啊,谢导,你看这石町桥像不像琴桥呀!”突然有一天我被眼前的景观所感染而浪漫地涌出一个感觉。“是,是很像琴桥!”谢导也被我的联想所感染,笑眯眯地坐在石町上长长地深思起来……
在我认识谢导时,这位已经在电影界辉煌了半个多世纪的大师早已名扬天下,然而竟然那么的平易近人,且特别的严格要求自己。相比之下,我们现在听说和看到的那些一夜成了些小名的演员们的“腕相”实在显得俗气和可笑。
照理说,像谢导这样的大师根本用不着自己亲自去拍摄地做那些踩点等基础工作,但谢导不仅不带一个助手,而且亲自跑每一个可能拍摄的景点。一次,当地人说有一座石町桥非常漂亮,但在大山深处,路很难走,建议年岁已高的谢导不用去了。我也劝谢导放弃,因为当时正值盛夏,气温高达三十四五度,我怕出意外。“我要去!要真是一个好景点,我不去怎么行?”
谢导非常执着,抬走就往山里走。那山道弯曲狭窄,一高一低,十分难走,稍不留心就可能倒在路边的沟谷里。当地的百姓听说谢晋大导演来了,纷纷从自己的家里抬出木椅、藤椅和扁担等,要抬着谢导往里走。谢导一看,想小孩似的一边笑一边逃,说:“我坐那轿子不成了南霸天了?不坐不坐!”老乡们和当地干部不干,说一定要抬他。最后拗不过,谢导便坐上了农民们抬的土轿子。于是我们浩浩荡荡地朝山里进发……在前往石町桥的路上和返回的途中,我特意看着坐在土轿子上的谢导,他是那样的不自然,脸都不时地红了,常自言自语地嘟咕:“我、我这不是成南霸天了?当年我拍南霸天,这回我自己当南霸天了……”老人那可爱劲越发让当地的乡亲们对他尊敬。
那一回,我们看到了一条最好看的石町桥。那些日子里,谢导和我几乎天天要出去看几座散落在山谷河岸间的石町桥,并被深深地感染和吸引。而“琴桥”上的故事也就这样在我和谢导的脑海里慢慢形成。最后我演绎了一个上海女知青因病不能到云南,通过亲戚关系到了浙南山区当知青,期间做了一位山村教师,后与当地一位农民出身的男教师之间产生了爱情并献身乡村教育事业的故事。作为电影本子的基本构思。谢导给予了认同,并且指导我不断深入演绎这个特殊年代发生的一曲山村爱情故事。这个最后有些凄婉的爱情,除了讲述那位上海女知青本人的特殊经历与特殊爱情外,后来又加进了她和那位山村农民男教师所生的女儿长大后到这个山区小学当志愿者时意外寻找到自己生父并立志留下当一名山村女教师的情节。许多剧情我特意设计在琴桥上,于是将此电影最后起名为《琴桥悠悠》,并特别得到了谢导的最后敲定。我和谢导都认为自己的电影故事很美,也很抒情,拍出来肯定非常艺术,并有深刻的思想性和普遍意义。当地政府官员和百姓听说了谢导要在他们那儿拍摄电影,并取名为《琴桥悠悠》,所以十分高兴,并从此开始将叫了几千年的石町桥改名为“琴桥”,而且言说是大导演谢晋给起的名。因为是好事,所以我也不想跟他们争这个“琴桥”的专利权了。泰顺县要借谢导的名气,利用开发以“老房子”、廊桥和琴桥三绝为主资源的旅游产业,我和谢导是非常高兴的。但由于这个地方经济十分落后,不能支持我和谢导将这一电影完成,从而也没有将琴桥最终地宣传出去,这是我和谢导的另一个遗憾。
谢导的遗憾还在后面。《琴桥悠悠》的剧本用去了我一年多时间,而谢导为这电影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则更多,占去了他最后岁月的许多时间。在这期间,谢导一面指导我不停改本子和看景,一面经常一起讨论用哪个演员来演这部电影。开始谢导告诉我准备用当红的“小燕子”赵薇和陈道明。后来这两人忙于其它电影电视,谢导放弃了他们。有一段时间台湾的女演员刘若英在大陆很红,谢导说他想用这位女演员。可有一回,我听他亲口愤愤不平地在嘀咕:“这年头,有些演员一出名就想着挣大钱,根本不知道艺术是什么。他们不会有前途的。”
从谢导的言语和表情中,我知道大师对当下的那些演员的所作所为很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一个真正优秀的演员,只能为艺术而献身,绝不能见钱开眼。
我知道后来的几年里,谢导一直在为我们的那部电影奔波操劳。开始由他自己的影视公司投拍,结果皆因经费问题停搁下来。我不懂电影的拍摄需要花多少投资,只认为像谢晋这样的导演还怕拉不到钱?然而我错估了这个时代的那些势利眼的能量。
是谢导老了?还是像《琴桥悠悠》这类反映山区教育题材的电影不合时势而没人理会?也许皆有吧。
我知道最初谢导想通过自己的影响力筹集拍这部电影的资金,为此他也拉着我去见了包括温州市委的领导在内的诸多政府官员和北京城里的企业家们,但最后都没有成功。期间我还收到了谢导给我寄来的他求助一位中央领导的信的复印件,我想这一回谢导有希望了,可等了很长一段时间仍然不见结果。记得2006年的一天,谢导在北京见到我,很无奈地拍拍我的肩膀,说:“看来我们的‘琴桥’要夭折了!”“不会吧,您老的面子那么大,人家还不给?”我不相信。谢导长叹一声。“建明放心,我会继续努力的。”那是我和谢导最后一别时他留给我的一句话。望着走向机场候客厅的谢导的后背影,我的心头顿时涌时一阵酸楚:一位献身于中国电影事业的巨人,已经83岁了,走路摇摇晃晃,却仍在竭尽心思为了一部不可能赚钱的“山村女教师”电影奔波忙碌,并且不惜拿着自己的老脸在到处苦求别人的“帮忙”……
2007年,我看到报纸上一则新闻:上海电影厂已经将《琴桥悠悠》列入当年度要拍的电影。可是这一年我最终没有看到《琴桥悠悠》正式开拍的消息。
又到了一个新年。突然有一天我在网上看到了谢导在一家宾馆内去世的噩耗……闻知大师的不幸离逝,我异常悲痛。而让我感到最难受的是:辉煌了一生的谢导,在他最后的日子里却无力去完成一部自己心爱的电影,并过早的带着这个遗憾进了天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