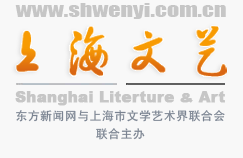董桥
董桥,福建晋江人,1942年生。台湾成功大学外文系毕业,曾在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研究多年。历任《今日世界》丛书部编辑、英国国家广播公司制作人及时事评论、香港《明报月刊》总编辑、《读者文摘》总编辑等职,现任香港一日报社长。
董桥历年在台湾出版的文集包括《另外一种心情》(远景)、《这一代的事》、《跟中国的梦赛跑》(均为圆神)、《辩证法的黄昏》(当代)等以及翻译书籍多种。另外在香港、北京、杭州、广州、天津、成都、上海及沈阳出版文集十多种。
到香港中环著名的中银大厦,叫一辆出租车,不过十分钟即到达香港作家董桥所在的香港半山区。
最初读董桥的书,有惊喜,《文字是肉做的》、《这一代的事》、《书城黄昏即事》等,与当时内地多数写作者单调直白的随笔相比,自有一种意境与巧思,恰如董桥自己所说的“追摹博杂,然后学雅”,其中一些文字得自传统处极多,然而读多了,问题也就来了,董桥的文章长处在雅,短处似乎也在雅,因为作者过于渲染那样的雅,过于渲染“旧时月色”,偏爱“飞案桃花只浮砚水”的意境,乃至于沉迷其中不能自拔,就像一直住在人工的假山园林中,总觉得少了些天然之气。况且,董桥总喜欢在文中夹杂太多的英文,于是渐渐也就放下了。
后来读到一位朋友私下讨论董桥的文字,才有些吃惊,顿时反思起自己的武断:“一位周先生评论董桥称其满足于‘将自己伟大的天赋用于渺小的目的’,这只是因为周先生没有读到董桥为‘伟大的目的’而写的文章。明白这一点,对董的‘非议’,如董桥有‘肤浅的文字优越感’,‘丧志到底的小文人’等,就不是对董桥说的话,而是对董桥的残缺不全的影子说的话了。这不怪周先生,也很难怪那些董文选本的编者,我们干脆就谁也不怪了吧。董桥在香港报纸开有‘时事小景’,在这个专栏里他写的当然不是有腔有调又吼又叫的文学,但也不只是‘肉做的文字’,不只是‘风格迷人,春色正好,触眼均是香车美女’,更不是论者断定的缺乏‘使命感’的文学。几年间两岸三地多少大事其实都在董桥笔底,不过他不写我们熟悉的社论,他只以自己的方式说该说的话。”
言外之意,其实是有着另一个董桥的。
到香港时,在湾仔淘书,终于淘得几本港版董桥文集,灯下捧读———这个董桥果然与印象里的董桥不尽相同,他可以建议当时的政府负责人“该读几本闲书了”,他可以从鲁迅旧居的枣树感叹“一国两制”,可以对金庸在杭州的访谈觉得不是味道而在文中反嘲“查先生前进得很”,真是意气风发,几乎让人怀疑这是不是那个躲进小楼赏古砚的董桥。
或许,这些是需要董桥自己当面解疑的———那天和董桥在电话里约访谈,他说:“到我家里来吧,这样随意些。”约定的时间是下午4点,自己提前了一些,下午3点50分,到半山区24楼的他家,揿响门铃,门开时,只见长长的客厅那头,瘦瘦高高的董桥正忙着穿一件黑色衣服,看到我,意料之中,然而似又有些意外,微笑着点头,匆匆把自己让进客厅沙发上,才说:“哎呀,和你约好的4点啊。”端来一杯茶,让自己稍等,又到里面不知收拾什么去了。
客厅四周全是字画,齐白石的、张大千的、傅抱石的,案头上陈设着紫檀木的小古董,阳台上似乎放着几盆蝴蝶花,面对中银大厦开得粉艳艳的———想象中董桥的家居就应当是这样的。作家出版社新出的董桥新书《故事》所写正是他在字画古董收藏中的经历与情感,从沈从文、张伯驹、张充和、袁寒云等字画的收藏经历中,透露出的“无一不是文化历史的侧影”,他自称那样的故事“仿佛民国初年微微褪了色的绢本团扇,我这一代人年轻的时候还沾得到淡淡一缕幽香,惘然中不无几分忭然。”
董桥终于来了,有些歉意地笑着,面对自己坐下,一团和气,言下之意似乎是“刚才的时间不属于你,剩下的时间就是你的了”,自然是从墙上的字画聊起,说起董桥的文字若与这些字画比,和齐白石当然是不同的,有些像张大千,或者说是溥儒,温润居多。董桥似乎并不否定自己这样的观点,说起收藏,顿时眉飞色舞,像个孩子,说:“我刚收了一件竹刻,真是精妙,给你看看吧。”捧出不知是明代还是清代的竹刻笔筒来,紫红得发亮,他的脸色也是红红的,小心翼翼地摩挲给自己看,那种满心的喜悦与沉迷让人觉得这到底是个性情中人。
看过了一件,再看一件,又领着自己品赏悬挂在书房里沈从文的条幅、弘一法师的字、张大千的淡墨荷花……几乎所有的字画都是自己喜爱的,他收藏的沈从文章草条幅《赣州八境台》为古风体长诗,笔墨豪劲而古秀,神完气足,几近神品,文字后面那个平淡如水然而又倔强的“乡下人”几乎触手可及。
又说起《故事》,说起《从前》,论及中国文化,董桥不时提起胡适之、余英时,语气中满是敬意。他说1960年代在台湾时,参加胡适之的一个演讲会,演讲开始前,外面呼呼地刮着风,他看见窗子没关好,而窗子下坐的都是一些女孩子,有些瑟缩的样子,胡适便走下讲台,问那些女孩子说冷不冷,随后很自然地为她们关上了窗子,“这个细节一直留在我的心里,也一直让我感动,其实我想做的,就是做中国文化的‘关窗人’。”他说。
董桥语录精选
谈“爱书”
人对书真的会有感情,跟男人和女人的关系有点像。字典之类的参考书是妻子,常在身边为宜,但翻了一辈子未必可以烂熟。诗词小说只当是可以迷死人的艳遇,事后追忆起来总是甜的。又长又深的学术著作是半老的女人,非打点十二分精神不足以深解;有的当然还有点风韵,最要命是后头还有一大串注文,不肯罢休!至于政治评论、时事杂文等集子,都是现买现卖,不外是青楼上的姑娘,亲热一下也就完了,明天再看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藏书家的心事》(《这一代的事》)
谈写作
写作如练琴,非日日苦练数小时不足以言“基本功夫”;无基本功夫者,虽情感如水龙头一扭而泻,究无水桶盛水,徒然湿洒洒一地水渍耳。一日,有客问中台港三地文风之区别,笑而答曰:大陆文章一概受阉割,枯干无生机乐趣;台湾文章底子甚厚,奈何不知自制,喜服春药,抵死缠绵,不知东方之既白;香港文章则如洋场恶少之拈花惹草,黑发金发左拥右抱,自命风流,却时刻不离保险套,终致香火不传。香火能传最是要紧。———《书窗即事》(《这一代的事》)
访谈
真正写出一种风格是很难的事
东方早报:内地读者对你的印象似乎有些片面,包括这次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专谈收藏的《故事》,或许让不少读者都加深对你固有的印象———那就是认为董桥遗老气太重。你的另一面,比如那些时评的文字,其实并未被内地读者了解。
董桥(以下简称董):我比较倾向传统一面———传统当然有西方的传统,我的教育一半是英文一半是中文,英文教育受得久了,对人生、政治、国家的看法,自然会倾向于西方个人主义,这免不了,我也不想改。
我从小在殖民地长大,小时候在南洋,说荷兰话,后来到台湾读书,再后来到香港,这里有个好处———放任,但还是有一个框框在那里,比如《香港基本法》。英国人定下来后,文本不会动,一些东西你可以稍微松动一些,当然英国人也没有给香港人真正的民主。我觉得内地对回归后的香港是比较宽松的。有些东西过去写时评时说得很多了,现在再讲也没什么意思,像我这样的读书人能做什么呢?我已经老了,我就等明年退休以后,收藏、写写字画,写写小说,做自己想做的事,有很多东西我看不顺眼,但时代在变,比如现在到处用电脑,但其实看一本书与看电脑是两回事,书会让人守得住,书有书香,所以我看到黄裳先生、杨绛先生,这些都是我很尊敬的,这样的老人现在很少了。
我以前想不通沈从文文章那么好,为什么要放弃写作研究古代服装?现在似乎有些想通了。
东方早报:其实沈从文放弃写作内心也是无可奈何的。
董:对,现在香港的情况也是这样。朋友太多,讲得多了也不好。
东方早报:现在还写时评吗?
董:不写了,报纸读者群越来越中产,媒体变了,要让年轻人去做,我和他们说:“你们去闯吧,我只定大的方向。”从人生到工作,再到写作,自己的心态其实是一贯的。东方早报:换句话说,就是你不太在意大陆读者对你的评价?
董:是的,文章写出来作者就“死”掉了,写出来人家评那是人家的权利,但自己不用太认真,除了做学问、写文章要认真。我想做的就是遵从自己的内心,你的内心世界可以不受任何人干扰,内心需要培养得越来越好。
东方早报:这些观点的形成与现在年龄有没有关系?
董:应当有的,年轻时不一定有平和,现在平和多了。你说旧书,上海还可以买到,施蛰存留下很多,我收的是西方的古书,黄裳先生收藏的中国古籍多,他那时的机遇好。
东方早报:我觉得你的文字与张大千相品,温润。与齐白石的路子不同,整个风格与大千的风格可能较为相契些。
董:是啊,与大千小品,个性决定一切,溥儒你留意过吗?也很好。
东方早报:是的,溥儒在宋元画方面下的工夫太深了。对于书画收藏的喜爱,与你练习书法有没有关系?
董:应当有关系,我从小就开始练书法,那时写何绍基的字,不过书法太难。上海书画界中,我最好的朋友是刘旦宅,他画的红楼人物真是一绝,书法也好,刘旦宅和大多画家不一样的地方是他用功读书,像这样的人越来越少了。大陆每天出那么多新书,我真正看得下去的很少了。
东方早报:是啊,现在出版界急功近利的还是居多。
董:余秋雨你觉得怎么样?
东方早报:早期挺好的,但后来似乎沉静气少了一些,我觉得他现在减少在各种媒体亮相的机会可能会更好一些。
董:余先生与我很好,也许是有一些误解的东西在里面,他名气大了以后,对各种活动其实可以稍微选择一下,比如跑到电视公司写游记,你说欧洲要有太多东西要挖,我在英国那么多年,都不敢说自己懂多少的。
东方早报:还是再说说你的收藏吧,什么时候开始收藏的?
董:我在台湾念完书就结婚了,1966年来香港,当时大陆的文物大多涌向香港,比我老的收藏家那时收藏了很多东西。1973年我离开这里,全家去英国,生了一儿一女,住到1980年才回来,当时做《明报月刊》,我这种经历与在大陆、或是从南洋回大陆读书的知识分子完全不同,他们的遭际与我完全不同,在英国那么长时间我发奋读书,在英国八年时间,那时真是很用功,从头想自己该读什么写什么。
要写好英文太难,要写好中文也很难,真正写出一种风格是很难的事。
东方早报:刚到香港时主要写闲情类还是时政类的文章?
董:1960年代来香港很苦的,那时报屁股文章要写,每天看外国杂志把文章译成中文,需要两三份工作才可以养家,不过当时也是一种力量———那个时候的香港很可爱,单纯,像小渔村一样,吃一碗面都开心,想想现在,太富裕了,但还是有很多不开心的东西。你看大陆经济发展后百姓的心态可能也差不多。
东方早报:说说内地刚出版的专门写收藏的《故事》吧,以前看你写过藏书票,不过这本书里更多的却是和文化名人相关的收藏。
董:我在英国收藏旧书、藏书票,那时在英国的中国古董很多,但我个人真正在英国买东西很少,直到1980年代到香港才买了不少。1960年代陪老先生看到很多东西,他们劝我们买。看中的时候,古董商收起来说:“小董,我先帮你收起来,等你有了钱再买。”慢慢就这样收,有一阵子古玉也收,还有砚台、竹刻,还有木的,黄花梨,都是文人喜欢的东西。前年开始,我开始收雕漆,是剔红的,这个最早是英国人欧洲人收,中国的古董市场新一代收藏家还没有充分发现,我看以后会热起来,这个东西艺术性很高,是还没有被发掘的艺术门类。1970年代我在英国看到很多八大山人、董其昌的字画,那时可能都是真的,但当时没有闲钱买———现在到哪里找?现在市面上的八大山人的画、董其昌的字画都是假的。有一阵子收上海画家的东西,主要是从民国初年到解放时的画作,但也难。真的好东西贵,应酬之作你也不想要。
张大千也是那时收的,张大千(好的作品)要到台湾去找,我专收张大千在1950年代的东西,1960年代都不太好了,1950年代字也好画也好。
东方早报:看你收藏这么多名人字画,想到那句话,写文章和书法绘画一样,其实只是写出自己。
董:我觉得自己的风格还没有形成,因为“我还可以写得更好”,写风景其实最难写,你看沈从文那些写山水的文字,多好。
东方早报:想想有意思,你在英国呆那么久,受西方文化的影响那么大,怎么会那么迷恋中国传统呢?
董:在外国住久了,就会发现你到底是一个陌生人,就想到自己的文化身份,加上从小家中就有传统文化的环境,我的父亲、舅舅啊,都喜欢书画古董,所以我自己喜爱中国传统文化也就成了很自然的事。
东方早报:那么对中国文化的定位与发展你怎么看?
董:中华文化的走向,最需要的是外来的营养,我觉得要重视余英时先生,余英时用西方的观念学术重新阐释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形象,让人启发很大,如果没有余英时先生的角度,中国知识分子的视角可能还是有些问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