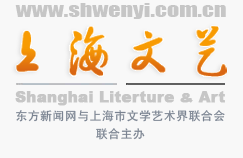――中国文联副主席仲呈祥专访
编前语:中国文联副主席、国家广电总局副总编辑、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师仲呈祥教授,不久前接受了本刊的独家专访。这位经由了文学、电影、电视等多维学理路径的学者,以他特有的睿智和历史使命,从审美的高度对当下的电视艺术作了精辟的分析,提出了自己精辟的见解。我们从中体会到思辨的力量的同时,更感悟到一种对中国电视艺术发展前景的期待与希冀。
时代艺术:对世界的审美把握
曲茹(以下简称曲):您的学术轨迹是从文学而电影而电视,从一定意义上说,始终是身处时代前沿艺术的研究领域。您如何看待今天电视艺术的表现和发展?
仲呈祥(以下简称仲):谈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回到一个古老的命题:人类需要艺术究竟是什么原因?这是需要重新考虑清楚的事情。只有人才会有独立的精神家园需要坚守。伴随着历史的进步、文明的演进,人类就形成了政治方式、经济方式、历史方式、哲学方式等把握世界的方式。与此同时,人们还需要一种审美的方式把握世界,那就是艺术。这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净化人类的情感,深化人独有的精神境界,从而使人类的精神家园更加理想化。正是从这样的意义上,黑格尔曾经说过:审美具有一种令人解放的功能,能够引导人类走向自由解放。这就是人类需要艺术的原因。所以,艺术的终极目标就是营造人类的精神家园,让人能够更加全面自由地发展。
现在,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传媒时代,这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高科技的普及,人们进入了视听文化时代,特别是以电视艺术为主要审美形式的时代。
曲:电视艺术从它的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时代的历史使命。当下,受众最多、影响最大的中国电视艺术,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失的组成部分。那么,如何让电视艺术更好地提高人们的审美情趣、塑造人们的审美品格并成为人们审美地把握世界的艺术手段?
仲: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这样认为:在人类的审美领域里,电视艺术成为了一门显学,它的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大、渗透性最强。符合逻辑的推论就是,如果人类电视艺术自身的思想品位比较高,文化内涵比较丰富,审美情趣比较健康、高雅,那么它作用于广泛的受众的鉴赏心理,无疑就会培养和造就一种不是浮躁而是沉稳的、不是肤浅而是深刻的、不是油滑而是幽默的欣赏心态。这种群体性的欣赏心态应当看作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明的主要标志,这是非常重要的。反过来讲,如果我们不注意对电视艺术的思想内涵、文化内涵和审美格调的追求,让思想平庸、文化稀薄、格调低下的电视艺术作品泛滥成灾,那么它将培养造就一种浮躁而不沉稳、肤浅而不深刻、油滑而不幽默的群体性的欣赏心理,就会造成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审美修养的滑坡”。为什么前一段时间,余秋雨先生会发出这种呼吁呢?在上海图书馆举办的一次演讲会上,他语不惊人死不休地说了几条意见,第一条意见就是,由于我们对艺术的轻视,已经造成了“当下中华民族审美的滑坡”。对艺术的轻视,在我看来很重要的一条是对电视艺术的轻视,我讲的轻视是忽视了对电视艺术思想内涵、艺术格调和文化意蕴的要求。就像大学者熊十力先生所讲的那样,“知识之败,慕浮名而不务潜修也;品节之败,慕虚荣而不甘枯淡也。”我们真正做学问的人应该耐得住寂寞,应该像真正的“为人民大众”的艺术家那样,为民族的艺术创作、学术积累添砖加瓦,我们不论是做学问还是搞创作都是一个目标——提升民族的素质,而不能造成民族素养的滑坡。我们今天要提倡一种严谨的治学风气,养成求实的学术操守,这对于每一位电视人都是非常重要的。
热播·收视质量·民族素养
曲:电视文化存在的问题与它产生的文化背景和作为视听语言的形态特征是否有着深刻的关系?
仲:人类进入这样一个以视听文化为主要的文化方式,或者在生存方式中占有很重要地位的这样一种客观现实面前,应该清醒地看到视听形象是作用于人的视听感官的,是一种具象。电视艺术对一般的受众来说是一次性的,稍纵即逝的,它只要求我们的受众对应地产生一种相对简单的时间观,比如我看一部《三国演义》,我会简单地联想到它是古代的事;我看到一部电视剧比如《和平年代》,我对应地想到这是我们今天的事。不像人类主要以书籍文化来传播文明的印刷时代,读书的时候是一册在手就可以反复阅读、深入思考。通过文字传播的文明是平面的,没有具象,作用于人们的阅读神经,激发相对比较复杂的时空联想以完成阅读。比如读《红楼梦》时,关于大观园的描绘都是文字的,每一位读者都会调动他的想象力来完成对大观园的想象。这样一来由于又可以反复阅读、细细品味,所以对于培养人的思维能力是更具有它的优势的,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强调,看电视剧《红楼梦》永远也代替不了对文学小说《红楼梦》的阅读。
如今的现实情况是,更多的观众把大量的休闲时间都花在了看电视艺术上,尤其在我们这个有着特殊国情的国家,中华民族对电视艺术还有一种特殊的期待。在西方的一些发达国家,电视对于相当的知识阶层来说主要是吸收新闻信息、观赏体育竞技活动。像中国这样电视艺术如此发达的国家并不是很多。但是我们今天的人民群众主要的文化生活方式,排在第一位的就是看电视文艺节目。面对着这样一种特殊的国情,要想代表人民群众提高素质的基本利益,要想通过电视艺术来体现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我们就必须以一种忧患意识来看待今天的电视艺术。这很可能是我与某些主张要用收视率来衡量,把收视率当成衡量电视艺术唯一标准的某些人的分歧之处。因为在他们看来,电视艺术只有受众越来越多,才能体现它的价值。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又有两个层面的问题需要弄清楚:一个层面是何为收视率?我们现在主要是靠着两家公司,央视-索福瑞和AC尼尔森。但他们的取样毕竟是有限的;第二个层面是很重要的,收视率和收视质量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收视率高未必收视质量高,而收视质量高,如果收视率也高那固然好,如果收视率未必高,它也有它存在的价值。比如两部作品,一部是我主张的那种作品,思想内容比较深刻,文化意蕴比较丰富,审美情趣比较高雅。如果只有100个人看,但这100个受众他们主体的修养都很高,他们看完后不仅获得了视听上的感官快感,而且通过快感达于心里,得到了一种认识上的启迪和灵魂的净化,由快感而升华到了美感。那么应该说这个收视质量是高的,我们可以通过讲这100个人的鉴赏体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人看。而且,这样的作品往往是可以反复播出的,是有生命力的。从长远看,它的收视质量是好的,因为它提升了受众的素质。相反,如果一部很平庸的作品,虽然拥有1万个观众,但是这1万个人都仅仅是获得了视听感官的刺激感,他们的审美修养非但没有提高,反而降低了,尽管收视率是前者的10倍,它的收视质量是不高的。那么作为对国家、对民族负有责任的电视艺术工作者追求的,当然应该是前者。我们现在的问题就出在这里,现在是需要我们冷静地、理性地进行分析,采取科学态度的一个关键时刻。
曲:我们来关注一个现在比较热门的《超级女声》,这个街头巷议的电视栏目某种程度上已经制造成为一个文化事件,如何看待它对我们受众审美情趣的培养?如何把握它与民族素质的关系?仲:这肯定是文化人应该深思的,如果作为商人那肯定是达到了目的,但一个有远见的、理性的民族,它绝不能用单纯的、商业的眼光来对待民族的文化。风靡一时的“超女”现象,收视率是很高的,有人会问,这个节目有没有给我们提供很重要的启示呢?我想如果在节目的运作上、形态的分析上能够讲出道理来,这是可以分析的。但是我要说明一点,艺术本来是不能搞运动的。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学就告诉我们,人类从事艺术鉴赏活动,鉴赏者是要进入“虚静”的,这是刘勰在《文心雕龙》里阐明的道理,而我们现在的做法是让鉴赏者首先浮躁起来,这是值得研究的。说某个城市有数以万计的女中学生为了参加这个选拔赛而旷课!这叫真正的艺术鉴赏活动么?另外,艺术是需要审美理想的,对于广大的热爱艺术的青少年说来,恐怕艺术应该导引他们通过勤奋的实践去健康成才,而不是让他们萌生一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警惕的“一夜成星”的投机心理。这是一个有责任的电视工作者应该思考的问题。
曲:这种情况似乎也是一种趋势,比如中央电视台的《梦想剧场》、《星光大道》、《非常6+1》等节目都是以普通观众作为节目的主要参与对象,电视节目通过让这些普通人进行一定的训练和包装之后,使他们有机会走上“星光大道”,其结果是掀起了一场场轰轰烈烈的“平民造星”运动。这样的节目往往是有市场的,不仅给电视台带来不菲的收入,观众也是赞赏有加。
仲:我个人不赞成这样的一种方式,特别是国家电视台,它应该担负起民族的责任。有一种说法,说现在是到了文化转型期了,意思就是说人类传统的审美习惯应该改变了,我认为艺术“为提升人的素质”这个方向不能变,《共产党宣言》里给我们提出来的:未来的理想的社会,这个集合体应该是以每一个个体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条件的。这是不能改变的,这是个规律式的解释。披着艺术之名而造成了每一个个体,特别是青少年个体精神滑坡、文化滑坡,这是对这个民族未来的损失,这是我不能赞成的。我更不能同意说它有存在的合理性。
曲:对于“超女”这类节目,我们可否换一个角度,只把它当成一种电视活动或者只是一种商业活动,从这个角度我们是不是可以更好地理解它所扮演的角色和所带来的影响?
仲:那么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商业活动对未成年人在其世界观的形成过程中的负面作用吧?你总不能否定它是一种文化活动吧?就算不是艺术活动,即便是文化活动,我们也应该努力地建设先进文化、扶植健康文化、抵制落后文化、清除腐朽文化吧?我想它算不得先进文化吧?甚至没有守住健康的底线。
曲:现在还有一个热点就是韩国电视剧,特别是最近韩剧《大长今》的播出又掀起了一个韩剧的收视高峰。透过这种“热”,我们能够看到什么?如何横向地看待其他国家电视艺术作品与我们作品的关系,以及对中国电视观众的影响?仲:一个民族适当地吸收兄弟民族的电视艺术的营养是应该的,“韩流”的出现确实有它内在的原因。其实《大长今》之前的几部电视剧,主要还是中国儒家文化的出口转内销,只不过呢,韩国创作者把他们借鉴、引入的儒家文化韩国化了,和他们本民族的精神相交融。当然韩国的电视剧也不能老是单一化,《大长今》就是通过一个医者的医道,从另一个角度写出了他们所崇尚的一种精神。我们经常处于一种错误的思维方式的控制之下,一会儿我们为了一个收视率走到一个极端,一会儿又在这个背景下,放弃自己的市场,拱手让给韩国的电视剧,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既然是要占领市场,那就用自己民族优秀的东西,借鉴别人是要有个度的。现在是一部两部、三部四部,源源不断地播出,连我们自己的电视人都在惊呼,我们宝贵的市场被占据了!那么回想一下,我们自己是不是就没有这个能力,或者说没有生产过这样的电视剧?我想就内容上来说,上世纪90年代的《渴望》也是呈现了道德伦理方面的内涵,而我们在宣传的力度上显然就不如别人,我们的《空镜子》这类的电视剧在思想艺术上也不亚于韩国的电视剧。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心是要强调的,在文化上自轻自贱,这样一个泱泱大国,13亿之众,是非常令人奇怪的事情。
创作者赋予了人物很多理想的色彩,人家在引导人,你看《大长今》要坐下来静静地看,“超女”是静下心来看吗?包括《还珠格格》,是静下心来看的吗?对自己民族的文化、自己民族的传统采用一种嘲弄、反讽的态度,呈现丑陋、揭示疮疤成了我们某些艺术创作者们审丑的目标。别人是在通过艺术强化对自己民族的历史、现实、伦理、道德的反思,我们是在纵容某些趋势和时尚,淡化民族对自己历史和现实的思考。某些电视人就在以这样的一种方式生产着“艺术”,电影也是这样。
审美化:电视艺术的诗意表达
曲:和所有的艺术形式一样,电视艺术之所以能成为艺术也是因为它所具有的审美性,它所有的艺术属性和价值规律都体现在电视艺术必须是一种审美活动,然而今天的电视艺术是否真的具备这样的质素?是否符合人们的理想诉求?
仲:作为理应成为标领这个时代中华民族艺术创作潮流的主要艺术形式的电视艺术,我认为缺乏了当代美学思想的支撑,也就是说,未能吸纳当代中华民族最高的审美思维成果,缺乏了这种理论素养的支撑。
中国电视文艺应该的方向,我觉得要防止一种随意的“西化”。现在有人用西方的媒体观念特别是西方的商业电视台、私家电视台的运营观念,来要求和评价中国的电视台组织的电视艺术栏目或者是电视文化栏目,这是我不赞成的。在我们国家,电视台是人民的、国家的电视台,是党和政府所开办的电视台,我们没有私家电视台,我们甚至也没有商业电视台,那么我们的电视台就应该为人民立言,着眼于民族的未来。在日本,他们的国家电视台、公共电视台NHK是连广告都不播出的,它的节目也很注意品位,绝不播出像日本商业电视台富士台所播出的那些品位低下的娱乐节目。邻国尚且如此,我们不该反省一下自己么?现在有一个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本台的商业利益的关系的问题,需要掂一掂孰轻孰重。我们中华民族的电视文化生态环境,是靠我们全国的数百家电视台共同营造的,如果没有了全局观念,一家冒出来搞了一种不顾思想品位和文化品位、格调低俗、单纯追求收视率、满足某些观众视听感官快感和刺激感的节目,那么一处破堤,效莠者会四起。于是乎,这个生态环境就会变得让人忧虑。这不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现实么?如果这个口没有守住,那我们就来比赛谁更能够消极地顺应某些受众的不健康的鉴赏需求,或者不着眼于久远的,不利于未来的鉴赏需求,那么这种只唯利的鉴赏需求就会日益强化,被强化了的鉴赏需求又会反过来刺激我们某些单纯追求利润的制作者,生产更能刺激观众视听感官的品位低下的产品。我们的电视节目就会处于一种节目生产和消费的恶性循环,也就是精神生产同文化消费的一种二律背反,我们千万别陷入这种悖论之中。
为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中央电视台编排了文艺晚会——《为了正义与和平》。我在《人民日报》上写了篇评论文章,我认为这是这么多年以来的一部经典之作,是可以和革命舞蹈史诗《东方红》相媲美的,的确体现了艺术的使命。艺术当然要给人们带来欢乐和快感,但是艺术绝不能止于快感。艺术的神圣使命是要帮助这个民族承担起反思历史和现实的重任,承担起通过艺术增强凝聚力的作用。由于艺术的这个责任,而艺术的使命又是靠从事艺术的艺术工作者及其他们为之服务的人民来共同完成的,所以由艺术的使命必然要想到艺术家的职责究竟是什么?因为这些老生常谈的事情如果不说清楚,对于现在的这些争论是分辨不清楚的。在今天,电视艺术作为时代的艺术,要在构建和谐社会中促进人的自由解放、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就必须高高举起社会主义审美理想的旗帜。共同的理想信念是维系和谐社会的精神纽带,共同的文化精神是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内在动力,而共同的审美理想则是营造艺术生态和谐环境的思想灵魂。社会主义的审美理想,就是要坚持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当成一切审美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提升人的精神素质、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当成一切艺术创作和鉴赏的宗旨。这就要求艺术家坚持“二为”和“双百”方针,坚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深入生活,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统一,既善于从博大精深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世界文化宝库中汲取精华,又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既立足本国,又放眼世界,大胆探索,勇于创新,着力表现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着力表现人民的大情大义和人间的亲情真理,创作出丰富多彩的具有强烈吸引力和感染力的倡导和谐理念、讴歌真善美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