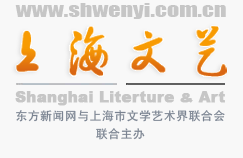北京墙美术馆,画展《失踪的美术史记忆》。入馆迎头看到的是在宋徽宗名画瑞鹤图中自然地拼接出天安门,接下来,你会在许多熟悉的画面中看到天安门,毛主席纪念堂,人民大会堂。天安门藏在普罗文斯山上(塞尚名画),毛主席纪念堂矗立弗拉基米尔路尽头(列维坦名画),人民大会堂则被寂静的修道院环绕(列维坦名画)。
表面上看,观众会认为这是关于古代与现代,西方与东方拼接出来的艺术。其实,远不止于此,这背后隐藏了一段失踪的历史,创作者王明贤苦苦追寻研究它已长达20余年。举办画展是为了唤醒人们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记忆,“这不是简单的画展,我在抢救红卫兵运动的美术史。”王明贤将自己收藏的大量罕见漫画以“放大”,“临摹”的形式,进行穿越时空的交流。
借文革题材进行当代创作,在美术界已经热闹了十几年并不新鲜,但从史学研究角度切入创作却不多见。受过系统艺术熏陶,多次投身中国当代艺术实践的王明贤把自己20余年的知识积累,借助40余幅作品表达出来。
“知识分子绘画是中国艺术史上很重要的传统,思考重拾失踪的文革美术图像的碎片,建构起超现实主义的‘文化性空间’,就有可能形成历史和当下的对话。”王明贤对南方周末记者说道。他把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称为“艺术考古学”,按照文化人物、电影批判传奇、设计革命等系列进行深入挖掘。
4月28日,画展开幕式上,青年艺术家王劲松谈及观后感:“不倾向绘画本身技术,不像美术品,更像艺术品。让人直接思考背后的内涵,很强烈,很好玩,解读也很直接。”展览共持续19天。
文革美术≠好玩
“临摹”——可能我既不深刻,也不好玩,但至少留下真实的历史。
展厅中《20世纪的回忆》,画面仅采用红与黑两色,很醒目。王明贤称,自己从这副画中读出中国美术界100年的沧桑。他“临摹”了1967年红卫兵批判齐白石的漫画,大师头像被一个破镜框裱起来,胸前戴着一串铜钱金元宝,左手竖起大拇指。在此基础上,王明贤添加了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展“不许掉头”的标志,他也是该展览的策展人之一。
“中国绘画发展从传统艺术到推出齐白石大师再到20世纪末现代艺术繁荣,我想其实这就是100年来中国艺术的符号。当年批判齐白石走艺术市场拜金主义,如今中国艺术完全被市场所操控,也是历史的悖论。”王明贤做出解读。
“我们这代人,包括蔡国强,徐冰,都受文革美术影响最大,给养我们的是社会主义艺术这一阶段,真正看到西方名画都到了80年代。”从1985年起王明贤开始收藏文革时期美术资料,如今他已经把1967年的《美术战报》、《美术风雷》全部资料搜集齐全。“我更加侧重1966-1968年的红卫兵美术运动,这是文革美术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段,而且在20世纪世界艺术上都是独特的篇章。但是这些资料基本已销毁,图书馆根本找不到,中央美院也没有这些报纸了。”
5年前,王明贤与严善錞、张颂仁联合在加拿大展出过藏品。在那次展览上,他意识到一个问题:这些在专业人士看来非常可贵的作品,由于年代久远,构图面积小,很容易被大众忽略,不会产生视觉上的震撼。王明贤决定以当代形式“放大”这些红卫兵漫画,去还原那段历史。
2005年,正在筹备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时,王明贤被查出直肠癌,告病修养,无法久坐,他开始了大量还原历史的创作。
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几大美院竞争非常激烈,王明贤他们常打趣:“列宾来参加高考不一定考得上,”喜爱绘画的王明贤报考了厦门大学中文系,但是他自幼随母学画,文革期间还拜过专业老师。
虽然因病偶然创作,但是画什么,怎么画却并非偶然。王明贤要借助“还原”历史的同时表达自己对历史的迷惑。
1993年,王明贤花10元钱在潘家园旧货市场买了张老照片,他原封不动“临摹”后成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画面上左为一个芒果,右边是毛主席,配有文字:外国朋友送给毛主席珍贵礼品——芒果。毛主席说:我们不要吃,要汪东兴同志送到清华大学给八个团的工农宣传队的同志们。
“如今当代美术家用文革资源创作的非常多,但是因为掌握资料太少,了解最多的都是文革后期的报头宣传资料,已被官方化,没有了文革美术早期那种粗犷有力的东西。”
他希望“临摹”后整体形象跟历史能完全一样。“不少艺术家对主席有各种诠释,但基本上都是歪曲的,扭曲的,变形得很厉害。用现代形式诠释我不反对,但不能太随心所欲。最后好像变得谁的胆量越大,越吸引人,这就不是当代艺术了。当代艺术的精髓是对历史,对主席有所思考然后呈现出来。”
还有一幅图,王明贤在主席像上添加了烂柯图棋谱,这是中国古代非常有名的围棋残局。“等于毛泽东与红卫兵的博弈,才有毛与所谓对手的博弈,这是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对毛泽东、文革美术我越研究越糊涂,都不知道毛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王明贤就是这样不断思索不断创作。
“当代艺术家,一方面使用很平庸的艺术资源,没有真正找到最有代表性的象征,另外有些作品做得比较浮浅。文革美术是很珍贵又很沉重的文化遗产,剪拼嫁接都可以,关键是要有反思,比如让人家想什么,一个艺术怎样打动人?可能我既不深刻,也不好玩,但至少留下真实的历史。”
真实历史就是以临摹的形式展现?面对记者疑问,王明贤以杜尚为例,如同当年杜尚把一个小便池直接拿到美术馆,在不同语境中就变成了新的艺术品。“临摹要加引号。我现在使用的是文化现成品作为素材,不是说自己画了多少油画,而是表现出的观念。比如说芒果这张照片背景,1968年毛主席重用红卫兵,后来局面大乱,又派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控制形势,并下达指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就有了送芒果的图片。”
如同他根据1967年批判电影漫画创作的电影批判传奇,经王明贤“放大”,统一用残破的胶片做框,黑边,白底,红色调,《五朵金花》、《阿诗玛》、《红与黑》这些影片时至今日都堪称经典。“历史就是这样不断反复与轮回。我们一方面会对红卫兵激扬文字感到特别好笑,荒唐,但有时候歪打正着,看到很多实际问题,又会产生幽默联想。”他希望原汁原味地展现历史,让每位看客自由去发挥创造。
“文革”美术主要分三个发展时期,1966-1969年红卫兵美术运动;以文革后期的全国美展和地方美展的开幕为标志,一批油画、版画、连环画作品被誉为样板;还有地下美术发展(无名画会,见本报2006年9月14日报道)。王明贤侧重的是一个时期,在他看来,这段历史犹如错版邮票。“中国美术史应该从50年代一步一步传承下来,到文革时期却突变,旧的被打翻。世界上从来没有美术学院院长、大画家被打下去,完全由学生做主的年代。这就是错版的美术史,独特,珍稀,价值就出现了。在艺术家眼里,文革美术只有两个字:好玩。而这实在是一段珍贵而又痛苦的记忆,一份太沉重的文化遗产。”
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拼接”——连这句话本身都是经人打扮的,太精彩了!
1982年,毕业后的王明贤分配到北京,任《建筑》杂志编辑。偶然听了一个讲座,涉及后现代建筑与当代建筑理论,他当时很激动,意识到原来建筑和当代艺术完全是相通的。那时候,他们一群有理想的年轻人们经常聚在建设部食堂里进行交流,1986年他和顾孟潮成立了中国当代建筑文化沙龙。“现在回过头来看,成员们基本上都是80年代中国最优秀的建筑理论家了。”这也被看成在85新潮美术运动中唯一的理论群体。
1993年,他又调任《建筑师》杂志做副主编,近10年工作中,王明贤侧重推出青年建筑师的实验建筑,并于1999年策划了中国青年建筑师实验作品展,涉及张永和,王澍,刘家琨,董预赣,汤桦这些人作品,相当于中国青年建筑师首次集体亮相。与建筑这份渊源,也体现在其作品的创作过程中。
《梁思成大屋顶悲剧》这副画就让人感慨万分。王明贤根据1967年建工部红卫兵漫画创作。画面上刘少奇的脸被抹去了,头上顶着重檐屋顶,预示中国建筑最高级别,手中握着一串宝塔等各种屋顶建筑形式。旁边的梁思成头戴单檐屋顶“帽子”,双手击掌附和。从上世纪50年代起,梁思成就倡导中国建筑的民族形式,被批判得非常厉害,称其复古主义,铺张浪费。这幅漫画就是以此背景而作,意为刘少奇支持梁思成,鼓励做大屋顶的建筑。
王明贤在原有基础上又添加了奥运会主会场“鸟巢”,中央电视台新址的造型,让人感觉到一股批判反思的味道。然而一直致力推广实验建筑的王明贤却不是这样考虑:“画这副画时很感慨,想想当时梁思成在建筑上稍微有点追求就被批判体无完肤,但是北京现在什么建筑形式都可以,从民族主义到鸟巢,央视,都是世界上最前卫的建筑,历史的变化太让人欣慰了。”
同样让他感慨的还有《真实的历史:1960年代现代化故宫改建规划》这副图,王明贤在1967年红卫兵报刊《城市规划革命》中找到当初提议拆故宫的方案图。当时对故宫改建共有6个方案,其中不乏建议保持外观,里面改成摩登现代设计,地面采用水磨石。但是最主要的当数这个第6方案,主张全部拆掉,然后按照故宫平面盖一个现代化办公大楼。他找到的拆迁方案原图很小,王明贤一直考虑怎样才能做出震撼的效果。他选择了拼接。
他在方案图上方附上了当年《地图战报》的北京街道图,那时候景山公园被改成红卫兵公园,到处都是人民路,革命路,工农兵体育场,还配有文字称北京是世界革命中心。王明贤用图说话,交代了当时历史环境。有了历史环境,还要有当下的思考,地图上飘着颗“巨蛋”(今年落成的国家大剧院)。“北京这50年来,从拆故宫,把重要地方都改成红卫兵符号再到盖国家大剧院,可能会有人读出里面历史的必然逻辑。”
上世纪50年代曾有人批判胡适说过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实际上后人考证半天,胡适也没有说过这句话。“连这句话本身都是人家打扮的,太有意思,太精彩了,我就是在这种状态下来解读历史的。”尽管王明贤不相信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引用历史部分时,他强调自己都像是写学术论文般严谨,但是展览中许多作品都展示了经过“打扮”后的历史痕迹。
这次画展涉及建筑领域的只是冰山一角,接下来,王明贤还会画一批红卫兵批判建筑的作品,结合他推广的中国实验建筑进行拼接。当时建筑界批判封资修和“杨贵妃”,都是独一无二的现象,“杨贵妃”是对“洋怪飞”的戏称,批判西方建筑都是洋派,造型奇怪,整个飞动起来。“原来北京有个和平宾馆,稍微用一点现代主义设计马上就被批得很厉害。”如今北京充满着各式各样的“杨贵妃”,历史评判标准真是任由人装扮。
中西方艺术的结婚证
“重写”——艺术地质学挖下去,很多政治,文化,艺术因素在里面。
在对历史与当今“临摹”拼接中,王明贤还“重写”了大量西方名画。“在我的作品中经常会有两种艺术史的脉络,呈现‘艺术地质学’的研究状态。”体现出来的形式往往是,列维坦金色秋天的名画中若隐若现地加上宝塔山,天安门如同海市蜃楼漂浮在库因吉名画的天空中,又漂到莫奈的“艾特达的日落里”。
“在对艺术研究过程中,我发现俄罗斯油画对中国影响非常大,从靳尚谊到我们这拨儿,文革中都是偷偷借到画册来临摹,列维坦是那个时期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画家,因为当时有种倾向,画政治题材,画人物都带有政治色彩,风景画显得更艺术更神圣,‘金色秋天’真不知道引领了中国几代油画家。另外,中国革命、社会文化与俄罗斯有着千丝万缕联系,但是发展又有中国本身乡土民族的东西,这就是艺术地质学,表面上一个是俄罗斯油画,一个是中国宝塔山,实际底下像地质一样深,挖下去很多政治的,文化的,艺术因素在里面。”
王明贤用超现实的手法把两个无关联的事物放在一起。“在世界名画上加东西,难极了,弄不好就画蛇添足。”这里远不是简单地添加,毛主席纪念堂矗立在弗拉基米尔路尽头,这是当年沙皇流放革命者之路,从这里走向西伯利亚。“所谓世界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终点到达这里,画上句号。原来天安门是古建筑,后来改为社会主义建筑群,到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后被划上句号。”王明贤诠释自己重写的意图。
“重写”大量俄罗斯油画之后,他觉得色调上有些沉闷,联想到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他又开始“重写”莫奈,塞尚等人的名作。当然要说勾勒出中西方文化关系的还当属《安迪·沃霍尔的中国结婚证》这副作品。初看到结婚证上的名字,好几个画家都以为是王广义当年的结婚证,只一字之差——王厂义。王明贤在潘家园旧货市场买到这个结婚证,觉得上面文字很有意思——为革命实行晚婚。有利于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利于更好地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积极参加三大革命运动为革命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有利于身体健康地发扬和成长。这让人联想到文革时期社会生活和政治种种问题,忍俊不禁,而王明贤思索不止于此,他联想到安迪-沃霍尔的波普主义与中国当代艺术的关系,于是这便成为了波谱之父的结婚证了。
无论以哪种形式还原历史,展现思考,王明贤还是反复强调展览的目的是呼吁人们对这段失踪的美术史资源加以抢救和利用。1993年,他去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看到的一幕至今难忘。其视觉中心建筑设计很奇怪,就有美国的小学老师拿着设计图边给学生讲解,边参观。“对于美术史,在西方看得非常重要,跟思想史,科学史一样,构成人类精神最主要的三大支柱。西方普通人受到良好艺术史、美术史的教育,他们从小要么到博物馆接受古代艺术,要么去当代艺术馆接受前卫艺术,进入大学后再接受艺术史系统训练。”
而我们的现状呢?“目前新中国美术史研究很不理想,其中因为特殊历史时期,一些研究成为空白,特别文革美术史,1966-1969年则完全空白。画家们流传着这样的段子:所谓艺术史就是艺术家拉的屎。对艺术史认知的重视,我们存在严重的缺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