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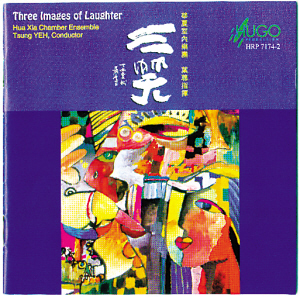
陈其钢和他的音乐专辑。
再度见到陈其钢,是近日在上海举行的《蝶恋花》专场音乐会上,当音符如花飘落,举座看着陈其钢,陈其钢却心无旁骛地看着台上。
作为当今少数几个在世界音乐舞台上极为活跃的中国作曲家之一,曾获封“现代派”的陈其钢在迈入五十岁之后变了性情。他诚恳地否定以前的创作,并对中国音乐传统表现出很大兴趣,近年不仅为芭蕾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创作了音乐,也写出将西方技巧与东方元素糅合的力作《走西口》《逝去的时光》《蝶恋花》……蕴涵浓郁文人气质的音符,一次次倾倒了西方观众。
在上海交响乐团休息室里,陈其钢谈五十岁后的自己,谈创作,谈他作为中方艺术总监正倾心投入的“外国作曲家写中国”活动,口气多平和,话语却屡屡闪现出思辨的光芒。
回顾前作:大多是遗憾
问:您在上海举行的《蝶恋花》专场音乐会,据说之前定的却是“陈其钢作品音乐会”,为什么改名?
陈:因为作品不够。
问:怎么可能?
陈:原来上交挑的是我的三部作品,但是,我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多满意的作品,便决定只把《蝶恋花》一个曲子演透就可以了。
问:多年来,您创作出很多有名作品,回头看,你怎么评价它们?
陈:过去6年里,我的大多数作品都留下了遗憾。当时以为自己了解音乐,了解想要表达的东西,写得意气风发,回头一看,才发现其实我根本不了解要写什么。
问:为什么会有这种感受?
陈:这与年岁有关。2001年我快到50岁的时候,在北京国际音乐节上首演了我的《蝶恋花》。当时,我在台上还不无得意地说,人到50岁便开始成熟了,对很多问题都形成看法了。现在我非常后悔这么说。一个作曲家是不会成熟的。他的世界应该是永无止境的。用一个短语来形容我现在的状态就是,五十仍有惑。
年轻时,我见生人很能聊。聊后就开始写东西,觉得“我了解了”某些事物。随着年龄增长,我越来越感觉到每个人的知识非常有限,传统的“我知道”很可怀疑。艺术家是需要自我的,但不仅仅是迷恋自我,更要善于怀疑自我。作曲家应该在充分怀疑自己的基础上,才会更客观、更冷静,而不执着于某种表象的东西。
重视传统:音乐不是“一加一”
问:近年您的创作,似乎比较多地融入一些中国传统音乐元素。
陈:20年前,我被西方音乐所召唤,然而在接近并了解的过程中,我感觉到作为一个东方人,我的精神世界里面有着一种不容抹杀的情结———关于本民族传统文化和音乐的情结。或许是远离,才让我感觉到对于传统文化和传统精神的更为贴近吧。在面对西方社会和西方音乐的时候,我突然找到了一些属于我们根子里的很宝贵的东西。
当然,传统和现代的结合,远远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简单算术,也许那更应是一种情结与情结交融的复杂过程。
问:移居法国多年,您的音乐中却越来越多地流淌着中国传统文人音乐所特有的那种惆怅、忧伤和怀念。
陈:儿时在北京,我跟姐姐两个人揣着电影票,乐呵呵去看电影,结果却被告知没电影放了。可是,如今回头来看这些琐碎的记忆,曾经属于一个孩子的失落,现在却也涂上了一层美好。时间总是替我们过滤掉很多不快乐,留下一些幸福在回忆里。
写作精品:巴尔扎克是老师
问:《蝶恋花》看来是你比较满意的作品吧?
陈:这个作品在欧洲演得很多。从当时写作的真诚度等方面来看,至今还没感到遗憾。但再过两三年,也许还会有遗憾。
问:会是哪种层面的遗憾?
陈:年轻时我非常内向。那个年代不可能有对于爱情,对于女性的深入了解。出国以后看到的世界很不一样,感受到的冲击很大,于是,开始逐渐感到我能够写出我所了解的女性了。所以,我设计了纯洁、羞涩、放荡、敏感、温柔、嫉妒、多愁善感、歇斯底里和情欲这九个段落,表现女性立体丰富的侧面。在写作上,不同的性格用不同的乐器、人声来表现。作品问世后,西方乐团认为,作品几乎像从另一个世界飘来的,几乎难以用已有的样式来界定它。
可是,现在感觉我了解女性还是很不够。就像大多数人年轻时总是倾向于喜欢年轻美貌的女性,长大了再看,便不一定了。巴尔扎克写《30岁的女人》,认为这个年龄以上的女性有了生活的历练,知道得到,也懂得给予,在各方面最为丰富,是“真正的花开了”。我觉得这是岁月给出的经验。写《蝶恋花》的遗憾,可能随着年月增长越来越强烈。
问:您似乎比较偏爱巴尔扎克?
陈:最近我一直在看他的作品和传记。巴尔扎克每晚8点睡觉,半夜12点却起床开始工作。到第二天上午,他又常把连夜写成的东西毁掉重写。也因此,他的每一部小说都写了5到10遍,一生留下74本著作,大多被公认为精品。要写出精品来,巴尔扎克的那股子劲,非常可贵。
欲毁作品:一生一佳作足矣
问:最近有欧美乐团翻出中国当代作曲家在上世纪七十、八十年代写作的曲子,集结成音乐会巡演,好像很受欢迎?
陈:说实话我挺失望的。拿了一部我上世纪八十年代写的很不成熟的作品出来演。尽管据说音乐会受欢迎,但是,观众其实不理解当年创作的情况。当然,也有人“自家的孩子自家疼”,还觉得挺满足的。
一个作曲家一辈子能写下一或两部伟大作品就很不错了。在时间的淘洗中,数量不说明问题,一定是质量起决定性的作用。但是,现在碰到的苦闷就是,欧美乐团演我的东西,哪怕是很差的东西,我没有办法来控制。
问:有没有可能改变?
陈:我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把自己认为不成熟的东西要么废掉,要么重写。可是,现在是一个“签约时代”。作曲家的创作跟音乐出版公司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你出一个作品,音乐总谱就靠出版社给你制作出来,改两次也许没有太大问题,但再要多改,就会觉得对不起别人了,因为每次都要废掉旧版重新制作总谱,就要重新投入。
巴尔扎克当年写了又毁的举动,曾让出版社非常不满,后来他干脆倒着给出版社钱。我想,对于那些经不住时间检验的作品,我不排除采取同样的举动。尽管,现在这样做可能比以前更加艰难。
热心为媒:跨文化写作擦出火花
问:这次与世博会征集音乐相关的“外国作曲家写中国”,您热心牵线,是何初衷?
陈:我们常在国外听到中国演奏家或选手演奏欧洲作品,作曲家也用西方的体例写作,听久了,觉得这不仅是学习和交流,也是西方音乐的一种传播方式和策略。这让我不能不萌发这个念头,如果我们邀请外国音乐家用自己的创作来表现中国音乐,在跨文化的撞击和交流中所产生的文化传播效应,也应该是双倍的吧。
问:这次的创作还给了音乐家们中国的旋律素材,会限制住他们的发挥么?
陈:我想不会。有旋律的创作曾被认为非常不时髦,但是,我认为旋律尽管不是音乐的一切,却自有它的生命力,我们不能回避也不应回避它。法国作曲家在进入新环境后受到刺激(包括接触中国传统旋律),每个人都进入了跟在法国不一样的创作状态。我想,这是一种交融。他们会赋予二胡、唢呐等中国乐器新的演绎可能性。他们不给作品贴政治标签,强调有感而发,强调有个性的音乐阐发,反过来也会对中国作曲家有所启迪。
相关链接
陈其钢,生于上海,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34岁时成为西方当代音乐大师梅西安的关门弟子,35岁获法国国际单簧管节作曲国际比赛第一名。1986年以来创作了近30部交响乐、室内乐、舞剧音乐。2001年管弦乐作品《五行》入围英国BBC国际作曲“大师奖”前五名;与EMI/VIRGIN签约发行全球的专辑《蝶恋花》,被世界权威古典音乐杂志《留声机》评选为全球十佳古典音乐唱片。2004年成为有着150年历史的法国斯特拉斯堡爱乐乐团的首位驻团作曲家。去年又在法国最权威音乐大奖“夏尔·克罗学院大奖”颁奖中,以新唱片《道情》获年度最佳现代音乐类唱片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