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协信息 |
|
| 经教育部批准,同济大学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上海市作家协会、上海市比较文学研究会等单位合作,将于2013年6月1—2日举办“从泰戈尔到莫言:百年东方文化的世界意义”国际学术会议,诚邀海内外学者与会。1、时间:2013年5月31日报到,2013年6月1—2日开会……
|
 详情
详情 |
|
|
|
|
|
|
|
 |
|
|
| 小说里人物的背景是知青身份,我写的是这代知青的当代群像和他们的当代命运……
|
|
|
|
|
|
点击进入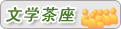 |
|
|
 |
|
 |
2012年09月26日下午,各国驻市作家来到上海作协大厅,与上海作家进行座谈交流。
|
|
|
|
|
|
|
|
|
 当前位置:作家访谈
当前位置:作家访谈 |
 |
| 贾平凹:我这三十年 |
| 2009年2月21日 10:22 |

贾平凹
我一生遭遇了四次大的争议,早期批我政治性不强,艺术大于思想,后来在反自由化中点名批我,又后来在清除精神污染中点名批,再就是批《废都》。我是受赞的多,受毁的多。几十年里每有作品出来都争议不断,几乎是在毁誉中成大的。——贾平凹
“抬头低眼看到自己的耻辱”
记者:你觉得你真正创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贾平凹:我产生写文章的兴趣是在西北大学读书期间,也就是1972年到1975年。那时整个社会的文学土壤很薄,陕西省还没有一家文学刊物,图书馆也不开放中外那些文学名著。写作可能是人类的一种生命兴趣吧,我那时偏就喜欢写作。这如在院子里倒了一堆土,虽然这堆土不久就得铲出去,而土里有散落的草籽或粮食种子,下了雨又晒了太阳,它就长出草和麦子包谷的苗子来。
那时兴革命故事,我写的东西变成铅印的是一篇《一双袜子》,是一篇革命故事,是和大学同学兼乡党冯有源合作写的,发表在1973年8月号的《群众艺术》上。这篇故事发表后,接连又发表了许多,到大学毕业时大概有二十五篇吧。这都不是文学创作。算作是一种爱好文学的练习,所写的内容已经记不起了,记起的是那时的热情。“废寝忘食”这四个字,在我后来的写作中从没有,却就在文学练习的那时候有。
记者:“废寝忘食”这四个字,让我想起你的大学同学冯有源在他的《平凹的佛手》里说到,您写作最初,也有“走麦城”、发不了的时候。那段岁月,您对写作产生过动摇吗?
贾平凹:写作最初,成名的欲望并不强烈,只是想能发表,那时寄出去的作品十分之九被报刊社退回来。但是,对写作没有产生过动摇。面对着一碗饭,人是会感觉出这一碗饭自己能不能吃完的,我那时自信我还能写的,总有一天会发表的,因为我读一些别人发表了的作品,常常并不满意它们的写法,我感觉我的想象力和文字要比他们好。
记者:孙见喜曾经写过,你“把那一百二十七张退稿签全贴到墙上,抬头低眼看到自己的耻辱”。
贾平凹:这些退稿签,一半是铅印的条子,有的编辑太忙,退稿签上连名字也未填上。那时当然也苦闷,很想把心绪调整一下。适在这时,各单位都要出人去市上修人防工事,这样,我便自告奋勇地挖地道了。挖地道真好,先开一眼猫耳洞,再四向开阔,又纵深掘进……我忽然问自己:创作也是这样吗?我的猫耳洞在哪里?后来,社里叫我去礼泉县的烽火大队蹲点,搞社史,当时真不想去,思想刚刚理出头绪,许多构思已经成熟,我急需的是赶紧写、赶紧写,担心到了乡下不可能有条件写构思好了的小说,而搞社史又是很乏味的,调查呀,座谈呀……但到了那里,和大队农科所的那帮年轻人,一起精屁股下河游泳,一起烧野火煨豆子吃,一起用青烟叶卷喇叭筒来吸,是很有意思的……后来,我依据这段生活,写了短篇小说《满月儿》,发表在《上海文学》1978年第3期上。
文学革命是必然也是必须的
记者:你因为1982年出版的《商州初录》,被认为是“寻根文学”的滥觞者。回到家乡,是你在着意寻找过自己的“根”?这种“根”又是什么?
贾平凹:在《沙地》、《好了歌》等那批反思社会的小说后,很快觉得没什么写的了,因为那些小说内容还不是我非常熟悉的东西,写起来不是那么得意。我检讨自己是文学上的流寇,应该有一块写作的根据地。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我返回了商州故乡,一个县一个镇的走了一遍,幼时的记忆重现,又联系所见所闻,觉得写写故乡的人和事,非常得心应手,就写起来,这便是《商州初录》。《商州初录》出来后,反响很好,自己就又几次去商州,记得当时去了以后找当地的一些朋友,毫无目的地走村串镇,饥了就在村民家吃,天黑了就投宿小店,住下了就在笔记本上记录当天的感受,非常的快乐。当然,不曾料想到,这一两年的生活使自己染上了病,此后十五年病才好,又经受了非常大的痛苦。寻找写作的根据地是我当时游历商州的目的,《商州初录》及“再录”、“又录”,和后边的一系列关于商州的小说、散文是这次改变写作方向的结果,而后来的“寻根文学”由一家刊物提出后,把我列入其中了。另外,在我的《商州初录》之前,我发表了我那时的一些创作上的想法,即《“卧虎”说》,那篇文章也被别人看作是寻根思潮中的重要宣言之一。
记者:回顾几十年的文学风潮,都是先有了创作,后被一些刊物总结后提出一个名称,再有意组织,就形成了风潮。对于这种一阵阵的文学风潮,你怎么看待?
贾平凹:最初写时,是没有想风潮这些问题的,当被评论家说到形成了风潮,盲从和模仿的就多了,以致越往后,这类作品就越失去原创性,流于故意写些过时的落后的东西,或徒有形式而内容空白。
记者:这段时间之后,应该说您进入了更自主的文学追求。当时有两股潮流,一是“先锋文学”,一是延续传统的写作,而您在这两股潮流之外。你怎么看待当时同代人的写作,你又如何坚持自己的主张?
贾平凹:《浮躁》之后,我虽然仍在写商州的内容,但对于像《浮躁》这种写法就结束了。《浮躁》的写法在总体上还是沿袭了20世纪以来流行的写法,也就是革命现实主义那种。但当时,“先锋文学”出现,势头很猛,国内文坛注意力都在那儿。我也热切关注着这种思潮,但我没有选择那种写法,又觉得一些先锋文学作品太刻意模仿西方文学,我不愿意在那方面努力。我的想法是:文学革命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在作品境界上,也即对于人的思考上、文学功能认识上、价值取向上,要借鉴西方现代文学,但形式上、根源上、趣味上一定得是中国的、民族的。我那时在这方面下的功夫很大。但这种辛苦实践当时没人理会呀,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在每一部长篇后都写很长的后记,主要在后记里谈我的一些想法。
人生的两次大浪
记者:您说您的人生经历过两次大浪,第一个是1970年您父亲被打成“历史反革命”而开除了公职,这件事情对您之后的写作与性格有什么样的影响?第二个是1984年患上乙肝在受到疾病困扰的时候,是什么动力让您坚持写作?后来的“《废都》之争”应该也是一个大的波折。这些是不是您对生活悲观的一个原因?
贾平凹:“文革”中父亲被打成“历史反革命”以后,我受尽了屈辱和贫寒,从那时我知道了世态炎凉。这一点使我在以后写作中对于生活的具体描写大有益处,因为当时性格极脆弱和敏感,到了写作时就特注重了细节。患过大病后,对于生命的东西体会很深。后来有了《废都》的事件,什么叫孤寂,什么叫痛苦,什么叫无奈,什么叫隐忍,我有体会的。这些当然会影响到我的人生观和处世态度。
记者:《废都》是您第一部城市生活题材的长篇小说,当时为什么会离开自己得心应手的农村题材?
贾平凹:原因有很多,一是那时我在农村生活过19年,在城市里的生活已经超过20年了,却还没有好好写过城市。越是有一种内疚,越是不敢贸然下笔,甚至连商州的小说也懒得作了。再者,农村生活不便于翻译,外国人太不了解中国的农村了。《浮躁》、《天狗》翻译到西方去,翻译者都感到很难,使我深感苦恼。城市生活中许多现代文明的东西是世界相通的,这对我是个新领域,我想再折腾折腾。
那时我已是四十岁的人,到了一日不刮脸就面目全非的年纪,不能说头脑不成熟,笔下不流畅,即使一块石头,石头也要生出一层苔衣的,而舍去了一般人能享受的升官发财、吃喝嫖赌,那么搔秃了头发,淘虚了身子,仍没美文出来,是我真个没有夙命吗?我那时实实在在地觉得我是浪了个虚名,而这虚名又使我苦楚难言。要写出一部东西来,赶紧写,赶紧写。
记者:当时创作中的煎熬和快乐还记得吗?
贾平凹:那时动了写的念头,急着就像找地方下蛋的母鸡,苦于没个合适的地方。最后,是在1992年的7月底,我跟着剧作家景平,带着女儿贾浅浅,跑到了耀县这个名叫桃曲坡的水库,在水库管理处的平房里住了20多天。这是很吉祥的一个地方。不要说我是水命,水又历来与文学有关,且那条沟叫锦阳川就很灿烂辉煌;水库地名又是叫桃曲坡,曲有文的含义,我写的又多是女人之事,这桃便更好了。在那里,远离村庄,少鸡没狗,绿树成荫,繁花遍地,十数名管理人员待我又敬而远之,实在是难得的清静处。夏天的苍蝇极多,饭一盛在碗里,苍蝇也站在了碗沿上,后来听说这是一种饭苍蝇,从此也不在乎了。草蚊飞蛾每晚在我们的窗外汇聚,黑乎乎一疙瘩一疙瘩的,用灭害灵去喷,尸体一扫一簸箕的。在耀县锦阳川桃曲坡水库——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地名的——呆过了整整一个月,人明显是瘦多了,却完成了三十万字的草稿。
(《我这30年:10位文化名人口述改革开放》陈志红、陈志/主编,花城出版社2008年12月版)
|
| 选稿:芦村 来源:文学报 作者:贾平凹 蒲荔子 [联系我们]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