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协信息 |
|
| 经教育部批准,同济大学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上海市作家协会、上海市比较文学研究会等单位合作,将于2013年6月1—2日举办“从泰戈尔到莫言:百年东方文化的世界意义”国际学术会议,诚邀海内外学者与会。1、时间:2013年5月31日报到,2013年6月1—2日开会……
|
 详情
详情 |
|
|
|
|
|
|
|
 |
|
|
| 小说里人物的背景是知青身份,我写的是这代知青的当代群像和他们的当代命运……
|
|
|
|
|
|
点击进入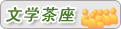 |
|
|
 |
|
 |
2012年09月26日下午,各国驻市作家来到上海作协大厅,与上海作家进行座谈交流。
|
|
|
|
|
|
|
|
|
 当前位置:作家访谈
当前位置:作家访谈 |
 |
| 袁敏:寂寞宁静地和历史重逢 |
| 2009年12月30日 11:19 |

袁 敏
33年前,一封伪造的“总理遗言”在全国人民手中迅速传抄,一桩单纯由年轻人游戏般起始的事件升级为国家级重大政治事件,一场强烈的政治风暴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33年后,该事件的亲历者、出版人袁敏提笔重述的《重返1976——我所经历的“总理遗言”案》一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近期出版。
自2006年6月在《收获》杂志“亲历历史”栏目发表《我所经历的1976》以来,袁敏追记“总理遗言”案的系列文章,一经推出即引来热烈反响。历经几次审阅和修订,文章结集终于得以完整面世,首印3万册已预订完毕,正在紧急加印中。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袁敏表示:自己所写的尽管是个人的历史,却未尝不可以深化历史,弥补宏大叙事留下的边角空白。“普通人不带任何目的的记忆,他们共同的追索,或许能为恢复历史的整体风貌提供具有史料价值的笔墨。”
记者:看完全书,感觉挺震动的。我想这种震动,与其说来自你讲述的“总理遗言案”,不如说来自于你经由这一事件引发开去的对时代、人性和命运等深层命题的感悟和反思;与其说你完成了对这一事件的追溯,不如说你追踪记录了那一重要时刻,及在当事人心灵和命运中投下的光和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书讲述的“往事”,远远超出了这一事件本身,时间才是它真正的主角。
袁敏:说实话,和出版社商定书名时,我确实在“我所经历的总理遗言案”和“重返1976”之间犹豫过。作为对历史的回望,前者无疑更准确,对读者的吸引力也会更大一些;但正如你所说,我在沉默三十年后首次触碰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不仅仅是为了完成对那段历史的追溯和记录。它所涵盖的一切超越了“总理遗言案”所带来的种种创痛和灾难,而更多带给我们的是从创痛和灾难的土壤中生发出来的美丽花朵!它们静悄悄地开放在大时代的角角落落,你要回过头去寻找它采撷它,就得切切实实地重新回到那个已经久远的过去,把当下的热闹和喧哗抛却,寂寞而宁静地去和历史重逢。你会发现,当时忽略或者看不清的种种,在重返的途中会不可思议地变得清晰起来。
记者:让我感触颇深的,还有你讲述往事的姿态。几乎出于人的本能,回忆过往,我们常常会不自觉地加以美化,字里行间难以脱开不胜唏嘘的怀旧和感伤。而你在写作过程中,似乎有种自觉的意识,要从这个窠臼里跳脱出来,你常常在看似可以尽情发出怀旧式抒情的关节处打住,转向对事件的追溯和反思。
袁敏: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一再提醒自己我不是在讲故事,而是在写历史。虽然我写的历史是渺小的个人的历史,但我相信,在历史洪流面前,亲历其中的个体能从不同的独特角度回忆历史、挖掘历史、记录历史,恐怕某种程度上也能深化历史,弥补历史宏大叙事留下的边角空白。也许正因为我始终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在写历史,所以我要求自己尽可能客观叙述。曾有人问我,文章发表时是不是做了删节,为什么总是读到关键时刻就戛然而止,像有很多未尽之言?我想,这可能就是你说的“打住”,假如其他读者也像你一样,在打住的地方停下阅读的脚步思索一下,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记者:伪造“总理遗言”的蛐蛐儿,即李君旭这个人物让人印象深刻。正是他的“双重谎言”,影响了很多人的命运。你的讲述提到了当事人对他行为的谅解,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和感动。但从写作角度看,放弃对他的“求全责备”,把责任推卸给时代,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对此事件的深入剖析?
袁敏:我想反问一下,你读了这本书以后是如何评价蛐蛐儿的呢?我想你不会因为我写了蛐蛐儿身上存在的某些人性中的弱点,就对他整个人的定位产生质的变化吧?我过去就一直认为,到现在也仍然认为蛐蛐儿是我们这一代人中的佼佼者,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他是一个真正的青年才俊。我们今天再回过头去看当年那份顺应了民心,张扬了民意,在客观上起到了像一把投向“四人帮”的匕首作用的“总理遗言”,你能不佩服这位遗言制造者的智慧和勇气么?你选择了“求全责备”这样一个词,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是说明你本身对蛐蛐儿当年的行为也充满了同情和谅解?我想,我们并没有把责任推给时代,但我们也没必要让个人来承担历史遗留的创痛。
记者:构成往事类书籍主体的通常都是备受关注的著名人物,你的新书围绕“总理遗言案”这样一个谜团式的事件展开,活动于其中的也多是普通而又不普通的人。这让你脱开人物钩沉,专注于事件本身的解析,从而获得了一种解谜式的动力,让人在阅读过程中有破解侦探故事的感觉。
袁敏:说实话,写这本书我脑袋里好像没有写作的概念,只是有一种喷涌而出想倾吐的欲望,有一种想打捞,想赶紧拽住,不拽住就会转瞬即逝的恐慌。尤其是当那些“总理遗言案”的当事人开始从这个世界上一个个消失,剩下的人也在慢慢老去的时候,这种恐慌尤甚,真的有一种和死神赛跑的感觉!
至于你说的有读侦探故事的感觉,那是因为这个历史事件本身充满了深邃的谜团,尘封的往事又过于重大,我不知道如何向读者诠释这三十年来的等待和沉默。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我和王旭烽一起去看望蛐蛐儿,想起他当年意气风发英俊潇洒的模样,再看他如今木讷迟钝失忆忘却的衰老,我一下子觉得,不能再等了,我有责任顺着这线头寻找谜团背后的真相。
其实我第一次写1976年的故事恰恰是小说,那时我还没有自信直面这一历史事件,然而发生在我生活中的种种已经在脑海里盘旋不去。与当年的小说相比,我更看重自己写下的《重返1976》的纪实文字,写小说时我好像飘在空中,有一种凄美的心绪在心中流动,而写这本书时感觉自己是踩在地上,很踏实,很有底气。我觉得这些纪实的文字更真切,更具冲击力,有更多思考。但同时我也承认,纪实作品有它的局限和束缚,当事人记忆产生的偏差,所处角度不同,或者有意回避,是构成纪实文学最具悬念也最有深挖意义的部分,却也是写作中最为艰难的地方。
|
| 选稿:芦村 来源:文学报 作者:傅小平 [联系我们]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