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协信息 |
|
| 经教育部批准,同济大学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上海市作家协会、上海市比较文学研究会等单位合作,将于2013年6月1—2日举办“从泰戈尔到莫言:百年东方文化的世界意义”国际学术会议,诚邀海内外学者与会。1、时间:2013年5月31日报到,2013年6月1—2日开会……
|
 详情
详情 |
|
|
|
|
|
|
|
 |
|
|
| 小说里人物的背景是知青身份,我写的是这代知青的当代群像和他们的当代命运……
|
|
|
|
|
|
点击进入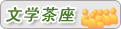 |
|
|
 |
|
 |
2012年09月26日下午,各国驻市作家来到上海作协大厅,与上海作家进行座谈交流。
|
|
|
|
|
|
|
|
|
 当前位置:作家访谈
当前位置:作家访谈 |
 |
| 韩东:作家的耐心与冒险 |
| 2010年6月29日 10:17 |

长篇小说转型之作《知青变形记》日前推出
早在2003年,长篇处女作《扎根》的出版,让韩东完成了从“诗人”向“小说家”最为彻底的转型,他作为小说家的才能和功力震动了文坛。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小说家韩东的每一次书写都显示出其优秀的文学气质,《小城好汉之英特迈往》《我和你》……绵密、冷静、克制又不动声色的“韩东特色”深入人心。
而近日由花城出版社推出的小说《知青变形记》,骤然让读者看到一个“陌生”的韩东。这部转型之作,让不少试图评价它的人困惑:“一切都是似是而非,深具历史感而又很难被严格的现实主义检验。”韩东说:“我一直期待某种结合,一己的意图和可供塑造的材料。”“一个全新的生命是完全独立的,它不是父亲或者母亲的影子,不以反映父亲或者母亲为己任,但无论是父亲、母亲都‘活’在它身上。”
相对于很多“小本经营”的作家,韩东无疑有一颗“大心脏”。在《知青变形记》之后,他关于乡村和过往生活的写作告一段落,他说自己还有三个长篇想写,“但无一例外都与乡村、下放无关”。
“转型就是它真正成了一部读者的小说,或者可供一般阅读的小说”
记者:读完《知青变形记》,第一个感受就是您“变”了。尽管仍然有鲜明的“韩东特色”:叙述冷静、克制,充满不动声色的幽默。但不再专注于对日常生活的细密描写,通过一个接一个荒诞的故事,呈现一个惊心动魄的“知青变形记”。是否可以具体谈谈“转型”?
韩东:从表面看,大概是“虚构”,故事以情节推动,现场感等等。最近和于坚的一次谈话深有启发,他说,《知青变形记》是让作者隐退,让“怎样写”隐退。也就是说,呈现给读者的是故事本身,是“写什么”。这不是说形式、方法、技巧等等的因素没有了,或者不重要了,而是隐退了,到了你看不见或者不易察觉的地方。《知青变形记》的转型就是它真正成了一部读者的小说,或者可供一般阅读的小说。只有作者或者内行人知道,这是更加需要技巧的。我的注意力逐渐向外转移,写作逐渐赢得更加广泛或者非专业的阅读,我认为这的确是小说之道,或者小说之道的开始。
记者:“文革”“知青”在我们整个民族的记忆中占据异常重要的地位。不是知青的人写知青,无疑是一种冒险。不少人在得知您的新作写“知青”时,既好奇又怀疑。冒险的动因是什么?
韩东:写知青只是一个幌子,主要还是写人。人和人在很大的方面是相通的,知青也是人,所以不存在所谓的冒险。写自己不熟悉的生活,其实只是一个准备问题,只要在材料、知识方面准备充分,并没有特别的难度。困难的在于杜撰,在于人物合乎情理的关系。比如在这本书里,一个大城市的青年学生由于命运左右转变为一个农民,难度和冒险都在这里了。我欢迎这样的冒险,因为有刺激,能激发出你的潜能。比如罗晓飞同意代替宋为国就经过了四道“门槛”,继芳的、为好的、福爷爷的和礼贵的。冒险也不是眼睛一闭再一跳,而是要具有耐心。在我看来作家的耐心就是冒险的资本,你甭想一挥而就。
记者:您用“总之一个单纯了得”来表示对已有“知青题材”文艺作品的看法,并希望自己的写作能给后人提供一个更复杂多义、深沉辽阔的想象空间。您认为导致那种单纯的原因是什么?
韩东:单纯和复杂都是针对人性而言的,针对情绪、情感、氛围以及结论性的判断。关于知青生活的描画,人们要么着眼于苦难,要么着眼于某种“浪漫情怀”,不是说他们错了,而是太简单了。知青的生活是复杂多义的,实际上人的生活都是如此。文学不是科学定理,以简单之美为荣耀,它可能是相反的东西,挖掘平淡无奇的表现以获得歧义和复杂性(复杂难言)。语言方式上可以简单、朴素,但情感、状态上不能简单。很多作品所努力的方向不免相反,语言方式极度炫耀之能事,但从人物到故事,从情绪到结论却如此简单浮泛。《知青变形记》试图把某种颠倒再次颠倒过来,该复杂的复杂,该简单的简单,不可以文害义、文过饰非。
记者:评价您这部小说时,诗人于坚有这样的表述:“它不是韩东一向擅长的那种小说……这是一个作者相对于自己的独创,一切都是似是而非,深具历史感而又很难被严格的现实主义检验。现实主义这把尺子插不进去,因为小说创造的一切细节都是自足自在的,超现实的、荒唐不经,但是自圆其说。”这是不是您所说的“一个小说家,有责任连接历史和想象,连接真实与虚构,在二者间架设一座交汇的桥梁?”
韩东:于坚说得太好了。这不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只是运用或者模仿了现实主义的笔法或笔调。实际上我一直期待某种结合,一己的意图和可供塑造的材料。这不是现实主义,而是和现实交流、交往的一种结果。只有在交流、交往中才能产生强大的生命力,它(作品)不是父本的,也不是母本的,而是父母结合产生的一个全新的第三者。作为一个小说家,我从不相信单性繁殖,囿于自我天地的纯洁不是我期望的。当然相反的,纯粹客观镜子式的现实主义也是一个陷阱,那不过是一种代孕。相对于《知青变形记》这部作品,我是真正的母亲,但需要来自父亲的基因。这一比喻也可以回答历史和想象、真实与虚构等等的问题。一个全新的生命是完全独立的,它不是父亲或者母亲的影子,不以反映父亲或者母亲为己任,但无论是父亲、母亲都是活在它的身上的。请注意这个“活”字。
“我的责任感只是作为一个社会人的,一个普通人,不是作为一个作家的”
记者:尽管您一直说自己的努力只是为了探究小说本身的神奇和魅力。可读过作品的人都会被您作为作家的责任感所叹服。以超越历史的态度描写历史,这体现您对当下现实怎样的思考?
韩东:我真的没有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感。我的责任感只是作为一个社会人的,一个普通人,不是作为一个作家的。作为作家的责任感也有,就是尽自己的力量把东西写好,而不是凭借自己特殊的技能或者影响力去左右天下大势。对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以及人类历史我持保守的悲观态度,涌现在我脑子里的词大概是“不可救药”或者“罪不可赦”之类。当然我是其中的一员,逃脱不了责任,但这责任首先是认罪,而非任何改良的意图。我作为一个人的责任也许就是始终坚持自我渺小、局限、性恶以及不堪的认识。爱人类可以,但千万不要自爱。怜悯他人可以,但不要自怜。这便是永恒的当下现实。
记者:在整部小说中,主人公罗晓飞的性格与其遭遇的残酷命运呈现极大反差,他面目模糊甚至有些逆来顺受,没有我们常见的在激荡命运下的性格鲜明的爱恨仇怨。仔细想想,其实由这种反差带来的张力,更能彰显民族伤痛和世态苍凉。有人说:“荒诞乃是存在的自然本性而不是一个批判对象,这是韩东抵达的深度。”具体在罗晓飞身上,您认为他是通透的还是妥协的?当下的很多年轻人在一次次理想与现实碰撞后,大多会发出一声感叹:人的成长注定是一个不断与社会妥协的过程。
韩东:简单地说,一种妥协是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强,变成压迫者的一部分。另一种妥协是越变越弱,以至于最终觉悟。罗晓飞属于后者,他的顺从开始是行为上的,最后变成了一种心理。不说觉悟,离觉悟也不远了。于坚说得好,荒诞并不是一个批判的对象,对荒诞的批判是一种抗拒,而人在抗拒中获得力量,如果有朝一日他战胜了荒诞就变成了荒诞本身,变成了另一些人深感荒诞的原因。抗拒恶梦者最终变成了他人的恶梦。有一句话叫做: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现在的年轻人,所谓理想与现实的碰撞都有一个前提,就是功利的不证自明。人人都在追求功利,在此一点上不加怀疑,所以他们即使向现实妥协也要有利于功利。变成强者、压迫者、坏人,变得庸俗、伪善、丑恶是题中应有之意。越变越弱的人,在心理上彻底放弃变得强大,并觉得这样甚好,现在还有这样的人吗?有这样的觉悟或者妥协吗?有这样的但求无过吗?这就像是在地道里,有一条道越走越宽,但终究是死胡同,而另一条道越走越窄,但通过最狭窄黑暗的部分后就来到了地面。我们都在地道之中,都得匍匐前进,但姿势和方向是截然不同的。
记者:《扎根》《小城好汉之英特迈往》《知青变形记》这三部小说,与您1969年随父母下放苏北农村的那段经历有关。从8岁到17岁,那段时间也是每个人性格成型的关键阶段,会对人的一生有很深远的影响。
韩东:童年到少年时期,我在生产队、公社和县城都待过,因而对中国农村的基层有某种直观的了解。在传统上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新一代的城市人大多来自于农村,因此作为一个写中国故事的小说家,这段人生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并且我所经历的农村是土地改革后的农村,同时也是改革开放以前的农村,其地位比较特殊。这是某种过渡时期的农村,传统社会崩塌,革命和政治因素的介入,使得我经历的农村生活极富戏剧性。并且说到底,我是一个在那之外的人,至今也已经几十年没有回去过了。这种时空因素皆有的回望,使我更能了解当今中国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以前相信天才,后来相信大师,现在我相信匠人,也只想做一个匠人”
记者:从1995年出版第一部小说集开始至今,已有15年了。而从1980年写诗开始算起,您的写作已经坚持了30年。三十年的写作,对它的理解和态度有何转变?
韩东:这个问题很有意思。现在,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职业感,在年轻的时候不知道,以为文学只是讲究天分。天分、技巧、才能,甚至方式、方法都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是职业状态。以前相信天才,后来相信大师,现在我相信匠人,也只想做一个匠人。每天工作,反复斟酌、琢磨,严肃认真,不惜工本,相对固定的程序、流程,总之要笨一点,甭总想着走捷径。你花的力气、工夫是能看出来的,是蒙混不过去的。在写作的要素上我现在排第一的是工夫或者功夫,功夫是要花工夫才能获得的。下面,才排到方式、方法、技术之类。才能排在最后,虽然它是我们开始启动的资本。
记者:对于长篇小说的写作来说,如何让气韵贯通始末是一个高难度的技术活。您的小说总让人感觉气韵十足,从头到尾都很充沛,这也是能吸引人一口气读完的原因之一。您是怎么做到的?对自己的小说有怎样的期许?
韩东:你读得快活,我写得艰难。这是成反比的(至少在我这儿)。我越是艰难,为每一个字词备受折磨(这不是比喻),就越知道它到位之后的效果。我有多艰难,文章就有多平滑,你阅读的时候就有多飞翔。光飞翔还不行,还得挂得住,就是想停就停,停在任何一点还有风景细节可看。所以,这的确是很难的。我对小说的期许实际上已经说了,就是要写出我自己认为最好的小说。连自己都不爱读的小说我是不写的。而那让自己无限陶醉的小说才是值得我努力获取的。
记者:您主演过电影《好多大米》,写过电影剧本《在清朝》。今年还成立了“韩东剧本工作室”。很多人都感叹,为什么韩东可以做那么多事情?
韩东:剧本工作室是几个朋友临时起意。我倒的确是想尝试和各种艺术方式的合作。这种合作能打破僵局,刺激热情和潜力,也渴望创造出不一样的东西。我做的事并不多,只是一直在做而已。有句老话叫做:只怕站不怕慢。站住停止时间就过去了,但你慢一点没关系,只要一直在做,积少成多,就蔚为大观了。再者,我明年五十岁了,正是一个作家的最好的时期,经验与精力配合正进入佳境。但好景不长在,我深知道这一点。因此会尽量维系这一时期的。中国当代作家的“短寿”似乎已成定律,好在我觉得自己比较晚熟,也许有条件是个例外。
|
| 选稿:芦村 来源:文学报 作者:陈竞 [联系我们]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