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协信息 |
|
| 经教育部批准,同济大学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上海市作家协会、上海市比较文学研究会等单位合作,将于2013年6月1—2日举办“从泰戈尔到莫言:百年东方文化的世界意义”国际学术会议,诚邀海内外学者与会。1、时间:2013年5月31日报到,2013年6月1—2日开会……
|
 详情
详情 |
|
|
|
|
|
|
|
 |
|
|
| 小说里人物的背景是知青身份,我写的是这代知青的当代群像和他们的当代命运……
|
|
|
|
|
|
点击进入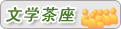 |
|
|
 |
|
 |
2012年09月26日下午,各国驻市作家来到上海作协大厅,与上海作家进行座谈交流。
|
|
|
|
|
|
|
|
|
 当前位置:作家访谈
当前位置:作家访谈 |
 |
| 张炜“心在高原” |
| 2011年1月31日 10:40 |

“450万字!中国最长小说你敢读吗?”某网站如此介绍张炜的新作《你在高原》。的确,这部史上最长纯文学著作有令人望而生畏的巨大体格,在喧哗与躁动的时代,有多少人能沉浸于如此斑驳而从容的故事,谁也没有底。
“真正的优秀作品,是不会被遗忘的。”读者的回答很响亮。《你在高原》8个月已发行8000套,并获8大奖项。面对这一成绩,54岁的张炜欣慰,亦淡然。他说,“真正的作家只会痴迷于写作,我听到的只有自己的心灵在回响。”
他是一个执着坚守的理想主义者,面对时代真实发言,表达人文精神追求。从上世纪80年代的《古船》,到90年代的《九月寓言》、《融入野地》,再到《外省书》、《刺猬歌》等,张炜质朴、真实而又如诗般优美的文字散射出智慧的光芒,也在一代人的心灵史上留下印迹。
《你在高原》从构思到出版花了20多年时间。沉下来,再沉下来,张炜一笔一划书写这几百万字的大书,正是源于他对文学的赤诚之心,这一点,在充满物欲诱惑的今天,尤为可贵。
多年以前,张炜曾在《融入野地》的末尾,如此写道:
“就因为那个瞬间的吸引,我出发了。我的希求简明而又模糊:寻找野地。我舍弃所有奔向它,为了融入其间。跋涉、追赶、寻问——野地到底是什么?它在何方?
野地是否也包括了我浑然苍茫的感觉世界?
无法停止寻求……”
在《你在高原》中,主人公宁伽用脚丈量大地,同时思索着人类永恒的精神困境,而在走向“高原”的过程中,作者的灵魂也得到了安顿。
“高原”这个概念统一了城市、乡村和原野,包括现实和精神两个层面
文汇报:10卷本《你在高原》去年3月出版时,其卷帙浩繁令人大吃一惊,质疑者称没有多少人会耐心读完。但8个月后,媒体和读书界回望2010年中文小说成就时,不约而同地认为,最“绕不开”的就是这部小说。作为作者,有何感想?
张炜:因为是几十年时间里写下来的,创作变成了日常劳动,所以作者自己并不会觉得太累、甚至也不会觉得它太长。它的原稿有600多万字,后来听从出版者的建议压缩成这样。作者在写作中从来不认为有什么不好读,相反常常觉得它过分好读了。实际上阅读感受总是千奇百怪的,哪怕是“最吸引人”的书,在有的读者那里也可能读不下去,味同嚼蜡。读者的素质和趣味不同,一本书不会面向所有的读者。所有的好书总要具备起码的深邃性,这概无例外。真正的文学写作是对读者和自己的双重尊重,更是一种自由的表达。
文汇报:一部作品的最后完成,少不了读者的参与,迄今为止,通读过这部小说的人有什么回馈?
张炜:其实书籍是不会因为阅读而改变品质的,这个道理虽然简单,但许多人就是不愿直接说出来。事实上所有的好作品,都是建立在这样的认识之上才能写出来。书出版之后,可以与美好的阅读沟通交流,这当然也是人生的愉快。但是这种快乐的预设最好不要出现在写作当中,那时更需要的是单纯和专注。现在书出版近一年了,作者直接或间接获得了许多交流,这让人感动。有人读得十分细致,甚至已经在读第二遍。作者一方面欣慰,另一方面又觉得太耽误他们宝贵的时间了,多少有些不安。如果作品是有价值的,那么真正的“回馈”一定是会放在漫长的时间中的。
文汇报:写作这部450万字大书的冲动最早来自哪里?
张炜:我在写《古船》和《九月寓言》时走了许多地方,主要是山东半岛地区。那时觉得有无数需要表达的东西,它们已经不能囊括在这两本书中了。我计划要写一部更长的书,但知道最终要完成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还有许多案头工作和野外勘察要做。再说,这既然不是短时间里能做成的事情,那就不妨把心沉下来、再沉下来。做到后者才是更重要的。
文汇报:“你”具体何指?“高原”有什么暗喻?“高原”是不是“我”一直在追问的生命和生存的价值和意义?
张炜:有的读者指出:书中的一些人向往并先后去了高原地区,这当是实指;另外也有精神层面的,就像苏格兰诗人彭斯的诗句:“我的心啊,在高原”。心的高原,这是不言而喻的。人在冗繁曲折的生活中对未知的苍茫有积极的寄托、有神秘的向往,是必需的、自然的,也是一种生命的属性。“心”不在此地,说明了对生活的不满甚至厌恶,这同时包含了再造生活和人生的强烈愿望。
文汇报:“我”向往“你”在“高原”,是否象征着个人对城市的逃离?
张炜:“高原”是苍茫大地,它也包括了城市。这本书正是用“高原”这个概念统一了城市、乡村和原野,是一个人依靠顽强和雄心所能够抵达的现实和精神这两个层面。
文汇报:《你在高原》这部书“为五十年代生人立传”,这代人有什么特质,为他们立传有什么现实意义?
张炜:书中有一个人物的话可做参考,虽然他说得不够全面——“……时代需要伟大的记忆!这里我特别要提到五十年代出生的这一茬人,这可是了不起的、绝非可有可无的一代人啊……瞧瞧他们是怎样的一群、做过了什么!他们的个人英雄主义、理想和幻觉、自尊与自卑、表演的欲望和牺牲的勇气、自私自利和献身精神、精英主义和五分之一的无赖流氓气、自省力和综合力、文过饰非和突然的懊悔痛哭流涕、大言不惭和敢作敢为,甚至还要包括流动的血液、吃进的食物,统统都搅在了一块儿,都成为伟大记忆的一部分……我们如今不需要美化他们一丝一毫,一点都不需要!因为他们已经走过来了,那些痕迹不可改变也不能消失。”我们常常认为这一代人经历的是一段极为特殊的生命历程:无论是这之前还是这之后,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这些人都将是具有非凡意义的枢纽式人物——不了解这批人,不深入研究他们身与心的生存,也就不会理解这个民族的现在与未来。
如上只是一个认识的角度。实际上每一代人都会认为自己是了不起的伟大一代,每一代人都喜欢把自己的经历看成是独特的。把自己的成就和灾难看成是划时代的和史无前例的,这也会妨碍他们的判断。我在书中其实就写到了对这种判断的怀疑。
文汇报:你的作品都有一种强烈的人文关怀意识和史诗性视野,是否有强烈的使命感,驱使你去做一个转型中国的记录者?
张炜:作家追求真理的恒念应当是工作的前提。但是他还应该有更丰富的趣味,比喻对复杂人性的强烈好奇心、对于诗境的痴迷和沉浸……不然一切都会是空洞和大而无当的。文学这种记录方式不同于一般的史书,它也许更复杂一些。它的主要功用大概也不是记录。一般来说我是回避“史诗性”的,因为我内心里同意海明威的嘲讽:所有二三流的作家都喜欢史诗式的写法。他起码在说传统的“史诗”模式。
写作者既要保持每次创作的冲动和新鲜感,又要有日常劳动的朴素心情
文汇报:《你在高原》创作中遇到过哪些困难?如此
漫长的创作之路,有没有想过放弃?
张炜:即便是一个短篇的写作也会有许多困难要克服,这么长的书自然要处理很多问题。放弃的想法是没有的,因为这只是一种日常劳作。劳动的快乐必然包含了克服困难和解决问题,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长期的文学工作一旦有了过于功利性的目标,出现阶段性的沮丧倒在其次,严重的后果一定是——最终的失败。
文汇报:“在写作《我在高原》的过程中,听到的只有自己的心灵在回响。”是不是这种内心的自在和创造的充实,推动你一笔一划认真书写下这450万个方块字?
张炜:创造性的劳动是愉快的,它通常有足够的魅力让写作坚持下去。写作者关键是既要保持每次创作的冲动和新鲜感,又要有日常劳动的朴素心情。这二者是需要结合起来的。一旦缺了前者,作品会“粘疲”;如果没了后者,漫长的写作生涯就不会很好地持续下来。
文汇报:这部小说跨越了超长时空,又涉及几百个人物,驾驭起来是不是巨大的挑战?你在接受采访时曾说,10年前写到某个人物已经死了,10年后忘记了。你如何保持小说架构的整体性?
张炜:它写了几百个人物,这要在细部一一记住是很难的,所以要全部完成以后从头核对。这主要是技术问题了,繁琐一些而已……几百万字的文字中,不仅是人物,其他的铆榫对接处也多得数不胜数,这都要耐住心性去解决。写作时要有足够的冲动,修改就是另一回事:不要写出一部就急于出版,而要待它全部完成之后,从头一点一点协调把握、细细打磨。
文汇报:你最后花了一年时间给全书挑毛病,出版社也找了5个编辑帮助大幅删改书稿,这个过程是否比22年的写作还要痛苦?
张炜:编辑没有删改书稿,他们只是建议和提出一些技术问题,由作者自己吸收和改动。他们对全书的帮助很大,付出了很多心血。
文汇报:你说自己只是一个作家,作协主席、书院院长等头衔只是挂名,那么这些经历对创作有没有正面的影响,比如在对转型社会的深度理解上?
张炜:这等于问“有没有负面的影响”——事物当然都是正反两方面的。总之既然要做,就要尽力,还要力所能及。这和写作的意义是一样的。任何事情都有难度,也都会有积极的意义。作家的主要工作还是写作,这不应该有什么变化。说到“社会转型”,我们会觉得中国上百年来一直在转型,从来没有停止过,人民怎样安居乐业?致富和社会变革不能过于峻急,如果一代代人都在巨大的颠簸中度过,哪里还有幸福?所以人们没法安心,而只好“心在高原”了。
现实主义和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主义不相悖,而大致是同一回事
文汇报:有评论家把你比作葡萄园里的哈姆雷特,笔下的“葡萄园”是植根大地的理想主义体现。30年的创作生涯,这是否是主线之一?
张炜:山东半岛地区是国际葡萄酒城的主要葡萄种植基地,我长期以来写的“葡萄园”是实在的,而不是什么比喻。因为我对这样的环境从小就熟悉,对葡萄园的辛苦劳动也习惯了,开手就会写到它。我经历的一些地方,常常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葡萄园,园子里是被生计累得要死要活的民众。这个环境在我看来没有多少浪漫,倒是经常想起斯坦培克一本书的名字:《愤怒的葡萄》。
文汇报:与以往的作品《古船》、《九月寓言》相比,这部书在创作手法上,有没有突破?
张炜:它们还是那两部书的继续。作者要一直往前走,伴随阅历的增加,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会有所变化,这是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作者是不会想到“突破”的,这是评论家才使用的两个字。
文汇报:《你在高原》是一部行走之书,用大量的调查还原生命的自然背景和生存空间,这对塑造人物有什么帮助?
张炜:虚构需要依赖现实,这就像粮食和酒的关系一样:造大量的酒就需要大量的粮食,但粮食不等于酒。作者在找大量的粮食,因为他想造出更多的酒。这个过程接下去是发生一系列“化学变化”,而不是“物理变化”。
文汇报: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和当下现代主义实践,是如何影响《你在高原》创作的?
张炜:现实主义和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主义不是相悖和矛盾的,而大致是同一回事。托尔斯泰当年的写作在我看来是“现代主义”的。《你在高原》植根于东部半岛地区的文化,准确点说就是“齐文化”。这并不是追求所得,而是无论愿意与否都要这样走下去,因为我出生在半岛地区并在那里长大,也就自然而然地接受了它的精神哺育。
最向往的是诗和短篇的写作,这才是最具有挑战性的工作
文汇报:结束了这段22年的“长途行走”,你说这部书使你的创作翻过了第一页,那创作的第二页是什么?
张炜:我因为要写《你在高原》,有些阅读和写作计划就要停下来。这部长卷只是《古船》和《九月寓言》等书的继续。现在我有时间按原来的计划和节奏去工作了,这就是接续原来的阅读和写作。我最向往的是诗和短篇的写作,这才是最具有挑战性的工作。
文汇报:你最早是以诗人的姿态登上文坛的,这30年有没有用诗写出了心中最重要的东西?
张炜:我一直在写诗,可是苦恼于表达的困境。现在我正在克服,这也带来了喜悦。同时,我认为小说与诗内在的核心部分是一样的,我好像一直在写各种诗。
文汇报:写惯长篇小说之后写诗,在文本上有没有落差?你曾说过一首好诗远胜于十车庸文,如何看待文学体裁的分类?
张炜:诗的地位还是最高的。当然如果小说的文学纯度如诗,小说的地位也会很高。但诗不是一般人认为的花花草草、不是所谓的“空灵”之类,而是人生最敏感的一次次面对——对全部生命秘境的透彻把握,当然包含了生死幽深以及锐利、黑暗和痛苦,许多许多……有人通常理解的“诗”过于简单了,他们不曾晓悟荷尔德林“黑夜里我走遍大地”是什么意思……
文汇报:万松浦书院还会坚持办下去吗?你认为自己是合格的“山长”吗?
张炜:那是公家的一个处级单位,正办得兴味盎然;它的发展取决于公家。不过,文化人的一己之力无论多么微小,都应该贡献出来。书院精神应该是知识人的梦想,
就这个意义来说,这里没有什么“合格”可言,而只有一个人的“梦想”吧。做事不能怕麻烦,需要一点耐心,还需要一些公益心。
文汇报:最近在读什么书?去年哪部作品让你印象深刻?
张炜:去年又读了再版的罗素的《幸福之路》,印象非常深刻。
传播手段与写作是两个不同的轨道:一个属于科技,一个属于心灵
文汇报:现在人们经常谈论作品与市场的关系,如几十万册销量与作品质量的内在关联等,你对此怎么看?
张炜:有人说在时下这样一个普遍阅读水准相当低下的情状,畅销书肯定是垃圾——有一定道理,但也不能绝对化吧。准确说,文学写作从来不是一桩买卖,就算是,那也要具体分析。八十年代我们参观上海闵行的一家合资玩具厂,那里当时正在制造各种玩具汽车,一箱箱产品装满了大卡车,而每一箱都装了几百辆“汽车”:这些“小汽车”都有模有样的,但其实只是玩具,内里并没有怦怦跳动的燃烧的发动机。将它们比作书籍也是如此,我们不能只看外表只听名称,而要看它们有没有燃烧的内在的发动机。所以,文学作品销售的单纯计数从来都是无意义的,因为道理很简单,就是要看它们是不是小孩儿玩具、有没有内在的发动机。有内在的燃烧的发动机的真汽车,一辆的价值相当于不知多少汽车玩具,说白了就是这样。
文汇报:网络作为“第四媒体”影响力日增,微博等社交媒体颠覆了大众生活方式,在浅阅读当道的网络时代,中国文学和整个思想文化需要坚持什么?需要改变什么?
张炜:一个文化素质相对低贫的农业国,对新的科技就会格外好奇和敏感。其实这无伤于真正的文学写作和文学阅读。因为传播手段以后还会继续发展,这与写作是两个不同的轨道:一个属于科技,一个属于心灵。文学轨道是从屈原、李白、杜甫那儿延伸过来的,也要按照自己的方向往前走,这是不会改变的。别说“第四媒体”,将来就是有了“第八媒体”,也仍然代替不了灵魂问题。作为一个写作者,也许他只需再次提醒自己这个浅显的道理:怎样阅读、多少人阅读,这一切并不能改变作品的固有品质。许多人一直在谈“网络文学”,哪有这样的“文学”?它并不存在,而只有文学——它们印在纸上、流动在荧光屏上,还曾经刻在竹简上、龟板上……如果总是热衷于分类“毛笔文学”、“瓦片文学”、“草纸文学”或“打字机文学”,这不是很无聊吗?
文汇报:史铁生去世后,你说过写作者的艰难和光荣,都体现在铁生这里了,史铁生作品沉甸甸的精神容量,恰恰是这个时代最为缺少的。
张炜:史铁生的作品一直专注于精神问题,苦苦求索,这等于对物质主义时代提示和强调了一种身份、一次说明:作家的时间很有限,所以不必娱乐他人、不必给那些只知满足于物质的各色人等提供服务,作家真的没有那么多时间,也没有那样的义务。不写作的人一直对写作的人强调各种“义务”,这真是有些可笑和荒唐。人要各自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文汇报:现在电子书很火爆,一些作品相继推出了网上阅读,你是否赞同纸本与网络同时发布新书的方式?
张炜:所谓的纯文学书籍一旦做成了电子读物,也只能用来检索和浏览,深入阅读和欣赏是不可能的。网上发布是一种宣传,可以促销。屏幕文字改变了人类千万年来形成的阅读姿态,要取代纸质书的阅读效果,那就要等待千万年的演化和进化。
文汇报:你觉得阅读媒介的改变会不会让传统书籍退出历史舞台?
张炜:印刷材质的改变虽然并不重要,但是纸质书很难被根本替代。从竹简到今天的纸走过了几千年,印刷或刻写的本质却一直没有变。几十年前有人惊叹说就要实现“无纸化办公”了,结果今天办公室耗掉的纸张却是以前的几十倍。这真是绝妙的讽刺。如果由此推理,那么新的阅读媒介只会极大地刺激纸质书的印刷量,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电子技术使纸质印刷更方便了,二是屏幕文字进一步引诱了纸质印刷的兴趣。
文汇报:你经常到国外讲学,怎么看待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问题?
张炜:文学主要是给本民族看的。文学“走出去”并非一定是好事,如果“走出去”的尽是一些“声色犬马”、一些浮浅之物,反而会带来可怕的民族误解。比如,我们许多人对于俄罗斯民族的理解和尊重,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从小阅读普希金、托尔斯泰等大师作品的结果。可见关键不是“走出去”,而是什么东西正在“走出去”。中国文学目前完全不必要急于“走出去”,这是浮躁和不自信的表现。就我们所知道的一些西方国家的好作家来看,他们当中越是优秀者就越是安于写作,从来不急于“走出去”。一个国家在艺术和思想方面的输出有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强大的人格力量、追求和创造完美的巨大能力,这些东西震撼和感动了其他民族,才算是真正地“走出去”,也是对世界的贡献。反之,如果只是让其他民族得到观察萎缩和渺小的机会、欣赏一群畸形的精神侏儒,那么这种“走出去”还是越少越好。
|
| 选稿:芦村 来源:文汇报 作者:梁炀 [联系我们]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