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协信息 |
|
| 经教育部批准,同济大学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上海市作家协会、上海市比较文学研究会等单位合作,将于2013年6月1—2日举办“从泰戈尔到莫言:百年东方文化的世界意义”国际学术会议,诚邀海内外学者与会。1、时间:2013年5月31日报到,2013年6月1—2日开会……
|
 详情
详情 |
|
|
|
|
|
|
|
 |
|
|
| 小说里人物的背景是知青身份,我写的是这代知青的当代群像和他们的当代命运……
|
|
|
|
|
|
点击进入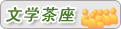 |
|
|
 |
|
 |
2012年09月26日下午,各国驻市作家来到上海作协大厅,与上海作家进行座谈交流。
|
|
|
|
|
|
|
|
|
 当前位置:作家访谈
当前位置:作家访谈 |
 |
| 宗福先:在舞台上向时代发问 |
| 2011年7月1日 10:39 |

宗福先
受时空限制,舞台戏剧能呈现的永远只是人类浩瀚历史中的森林一叶;但真正的戏剧大家却能以寥寥数笔的勾勒,让你观一叶而知秋。
33年前,两个小时的话剧《于无声处》揭示出的民心所向,如一声惊雷,打破了十年“文革”的沉闷;33年后,编剧宗福先与原班主创,将观众拉回到风雨如晦的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夜。在这场造成中华民族分裂,流血、冲突至今也没有完全结束的大事件中,由宗福先、贺国甫编剧,苏乐慈导演的《四一一·上海夜》,力图以几个青年人跌宕起伏的命运,表现重大历史事件背后的真相。
作为一个剧作家,宗福先一直试图在小舞台上寻找大答案:“这些无名者的牺牲,换来了今天的生活。希望在这个制度下受益的后人,能记住所有为理想献身的先行者。纪念这些人,想想这些人,现在的我们自然会有所为、有所不为。 ”
政治风波后的小人物命途
建党90周年、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之际,舞台、银幕、荧屏上的红色题材节目不少见。宗福先独具匠心,将目光对准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前那个月黑风高之夜。
“这个想法,来源于剧本创意毛时安。‘四一二’是中国历史重要的分水岭。在那之前,国共两党合作,聚集了一批热血青年,他们都愿拼将一腔热血来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现状。但是从‘四一二’这天开始,国共两党分道扬镳,由此造成的中华民族分裂,直到今天还没有结束。 ”
84年来,人们每每回忆起“四一二政变”,似乎很少想过当年那些“不重要的人物”的命运。宗福先认为,人类社会中一直有这样的规律:一场大的政治风波,会牵动无数人的命运。 “越是这种时刻,小人物身上的故事性、戏剧性越强。 ”
事实上,从33年前的《于无声处》开始,关注小人物就是宗福先创作的一大特点,例如他永远记住了古田会议旧址的两张照片。“有一次我随团去参观,看到了两张照片:一张上没有影像,只有一个名字,写了何时生,何时死,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第二张的那个人,1929年参加了古田会议,1930年就牺牲了。 ”宗福先回忆说,“这些东西后面有多少故事?今天我们讲英雄、历史,都很概念化。可是你看看这些小人物,没人记住他们,他们都跟我们一样曾在这个世界上活过,并且为理想而牺牲了。今天许多人在享受成果的时候把这些人忘记了,这是不应该的。所以,我想把这些被遗忘的事情讲出来。 ”
84年前的理想主义拷问
略显“落伍”的是,《四一一·上海夜》回归了《于无声处》使用的“三一律”,因为宗福先觉得“别的写法不足以表达我想要的”。
和写《于无声处》一样,设定人物后,宗福先开始在他们之间画起了密密麻麻的关系线:年轻美丽的女共产党员刘丹燕,盛传已被沉入江底的风流诗人马非,国民党二师参谋长赵翼平,还有不请自来的女佣人阿兰。他们出现在同一幢洋房内,距离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只有几个小时……“如何一层层剥皮让观众入戏?我想出个办法:四个人,一把枪,三声枪响,这就有了故事性,并把人物联系起来,派生出复杂的叙述。 ”宗福先说道。
“这出戏被话剧中心概括为红色悬疑剧,大概是因为阿加莎的悬疑剧演得火热,为了吸引眼球增加票房,也给加上了同样的帽子。 ”宗福先笑了,“但它确实是一部非常好看的戏。我一直觉得,主旋律的作品、娱乐化的作品,不该相互排斥,因为观众有各种需要。而且,主旋律的戏要更人性化更好看,娱乐性的戏却要增加分量。年轻一代不是不动脑筋的一代。我一直说,这是一个欲望的时代,但是年轻人并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这是一个娱乐的年代,但是年轻人并没有放弃严肃的思索。 ”
在宗福先的设想中,四个主人公会在话剧尾声走到台前,向观众剖白自己并提出反问。“比如女主角刘丹燕,她也许会这样说:我真喜欢现在的中国,我们那时候有很多很多理想,但也想不到现在的中国是这样的。一个人,只想自己过上理想的生活,那叫做欲望;但是如果想让别人都像他一样过得好,那就叫理想。我84年前这样想着,今天的你们也该想想,84年后的2095年,你们留给后代的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念出这段话后,宗福先顿了顿,自我解嘲道,可是他们都不喜欢这个结尾,也许用不上了。
人民依旧不会永远沉默
构思半年多,改了半年多,宗福先至今对新戏抱有遗憾:“我还是没有找到那句精神内核,如同‘人民不会永远沉默’之于《于无声处》,那样恰如其分、一针见血。 ”
说这话的时候,宗福先语速缓慢,这是典型中国知识分子式的儒雅凝炼——很难想象,他曾拿过无数次病危通知,全身有十六种病症,前些日子又查出了“眼睛玻璃体脱落”。“我自己非常知道,《于无声处》为我打底,也改变了我的一生。我一生多病,但正如一些人所言,我已经有了很多人一辈子努力都得不到的东西,因此不必再争其他。 ”宗福先说,“站过时代浪尖,徘徊生死边缘,好似活了几辈子,我已经完全想开了。 ”
宗福先的乐观是有底气的。 2008年,话剧 《于无声处》再次于上海话剧艺术中心重排。有年轻演员懵懂发问:“张春桥是谁? ”宗福先隐隐担心,那个时代的观念和氛围与今天有天壤之别,观众会不会笑话?没想到,观剧反响最热烈的竟然是大学生。有一场演出,宗福先前面坐着一对大学生恋人,男生看到剧中何芸等了欧阳平9年的时候,转头问女生,你能等我9年吗?女生断然回答:不可能。“他们在谈论中认为:我们太实际了,怎么能为了一句承诺等上9年呢?我想,他们是因为看这样的戏机会不多,才会被吸引,也引发了他们的思考。 ”宗福先说。
“后来浙大的学生剧社排演《于无声处》时请我们去看。大学生对这出戏很热情,我和苏乐慈导演受到的待遇简直是李宇春式的(笑)。我看到了现代年轻人的追求,他们追求崇高,也渴望崇高。我愿意做这样的一个人,这也是我和贺国甫写《四一一·上海夜》的重要原因。 ”宗福先说,“现在80%以上的社会艺术创造力竭力回避真实,远离政治。大家都在逃避什么?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作为艺术家,我们应该知道自己的责任与良心。 ”
抽屉里锁着时代的脉搏
宗福先不算是多产的剧作家,但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力图有所问,有所求,力图在历史浪花裹挟前进的泥沙中淘炼真金。在“天安门广场事件”未平反时写出《于无声处》,在改革浪潮呼声最热的时候写出《血,总是热的》……
在这之后,公共视野下的宗福先的选材渐渐转变了:电影 《鸦片战争》《意外事故》《高考1977》,话剧《谁主沉浮》,电视剧《寒夜》等作品,虽然依旧是现实主义题材,但却大多为回望历史。
“这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上世纪80年代初期,继《于无声处》《屋外有热流》之后,出现了一大批社会问题剧。很快文学界有了批判:认为过于急功近利,过于就事论事,没有历史的思考与文学的视角。我尝试过,但也许是自己功力不够,陆陆续续的,我写了《男人》《桥》等一些剧本,但被我藏了起来。”宗福先说,“当然,还有别的原因,比如脱离创作,公务太忙等。 ”
被宗福先雪藏的“抽屉文学”中,有许多光怪陆离的创意。如在剧本《桥》中,他认为他们这一代人是从封闭社会过渡到开放社会的角色,就像一座桥,是过渡性的,没有认可,也没有批判,看上去似乎没有什么意义。 “也许是我功力不够,反正没人愿意排。我就藏起来了,它们代表了我在一个时期的文化认知。许多事情也许并没有那么明确的是非,只能留待后人判断。所以到了现在,我还是一觉得有修改余地,就拿出来改。也许有一天能与观众见面。 ”宗福先说。
现在,宗福先已在酝酿下一个剧本。用他的话来说,这是一个“也许很尖锐”的本子。“管它能不能排、能不能演,只要我写出来了就问心无愧。 ”宗福先的语气平静但有分量。
|
| 选稿:芦村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李峥 [联系我们] |
|
|
 |
|
|
|
|
|